从诗学角度来看,无论舒婷一代还是伊蕾、翟永明一代女诗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将诗歌工具化的倾向,观念或者说身份意识在她们的诗学中占据了一个相当的位置。这种身份意识(舒婷的“一代人”身份,翟永明、伊蕾的女性身份)某种程度上妨碍她们进入更本真的存在。对舒婷那一代女诗人,诗歌是表现其社会意识的载体;对翟永明、伊蕾她们,诗歌则是表现其女性意识的载体——而这类意识固然有其切身的经验为依据,但也难免被一种以国际化面目出现的时髦思潮所诱导。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其文本的悬浮状态——文本化的经验和诗人、读者的切身经验存在某种隔膜和间离。也就是说,这两代女诗人的诗学中都有相当的社会学成分——其主流的诗学倾向,也许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社会诗学和女性诗学。而两代诗人在社会学关注点的差异以及文学进化论的潜意识也造成了两代诗人之间诗学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表现在写作上,也表现在批评上,甚至延伸到诗人的人际交往中。
池凌云这一代诗人的诗学出发点已经大相径庭。显然,生存经验的变迁和文学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当然离不开前代诗人已经做出的探索和贡献)使她们得以拥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无论对舒婷一代的社会诗学还是对翟永明、伊蕾一代的女性诗学,池凌云这一代诗人都有所吸收,同时也有所保留和警惕。比起前辈诗人对社会问题和女性群体的关注,池凌云一代诗人更加关注个体的、具体而日常的生命体验(而不是空泛的经验,更不是理论、观念的图解)。她们关注社会,但并不像她们的前辈一样试图寻找到某种社会学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她们面临的困境。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她们扬弃了第二代诗人那种对抗、对立以至敌视的思维定势——她们意识到,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受难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女性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包括男性问题的解决,否则便没有成功的希望。对她们,姐妹情谊固然重要,但这种情谊也不应该成为排斥某种兄弟情谊的理由。与其说她们关注女性问题,毋宁说她们更关注人的问题——她们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关心人生的整体,也关怀人类的全体。由此,她们把前辈诗人的社会诗学、女性诗学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体验诗学或者说存在诗学。她们关注的诗学焦点也由诗和社会、诗和女性的关系转向了诗和诗人、诗和读者的关系。池凌云无疑是这一代诗人中杰出的代表。我认为,正是池凌云这一代女诗人完成了女性诗歌由女性而诗歌的重要的意识转变。这一转变在周瓒身上表现为其诗学路径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某种转向——其标志性的成果即为完成于2001年的《黑暗中的舞者》。对于池凌云,这是一种更为内在、起源更早的倾向。就个人的经历而言——“娃娃亲”加诸个人身心的伤害,失败婚姻的惨痛经历——池凌云更有理由加入抗议者和控诉者的行列,但她没有。她选择做一个爱者,原谅了所有这些加于个人的伤害,为所有被伤害的人,甚至伤害过她的人歌唱。她关心的问题比所有这些伤害更大,比个人的幸福更广,也比生命更长久。她的心,比一个受伤的女性更悲哀,更柔软,但也更坚强——她所承担的是人世间所有的痛苦、悲伤和辛劳。她渴望拥有一颗广阔的“宇宙之心”,它“大过所有的心”,“但这颗巨大的心时刻都眷顾着最弱小的心。”①她为无名的受难者,为甘地和林昭所写的诗足以说明其社会关心的深度和广度;《游船》、《苦恼之夜》、《谈论银河让我们变得晦暗》、《无尽塔》、《流水没有带走光芒》、《自然元素》、《石头比从前更是石头》、《盲》、《安慰》、《在雾中》、《春天的所有安排》、《一无所知》等诗则表现了其深沉的人性体验,并向着宇宙生命打开爱与怜悯的心灵,其中包含着真正的神秘;《真正的树》、《到一棵树中去》、《阔叶林与针叶林》、《赞美》、《还给树木》则呈现了另一种亲切的自然体验……其诗歌关怀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女性诗歌中恐怕都是鲜有其匹的,其诗歌风格和美学风貌也因之呈现出女性诗歌少见的丰富性。
当然,这种对存在的广阔关怀并不排斥池凌云的诗歌仍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女性特质。然而,其表现的形态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实际上,所谓诗歌的女性特质在池凌云的诗中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舒婷所理解的温柔风格,也不仅是翟永明、伊蕾所抱持的反抗美学。它包容了温柔,也包容了反抗,而将之转化为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一种基于女性的特质而又超越于女性之上的爱。池凌云的诗虽然对男性读者开放,但在多数情况下,其诗歌的隐含读者仍然是女性的。这也足以说明,女性问题仍然是诗人一直悬心的重大问题。她说:“仙女与天使是一对姐妹。当所有姐妹都安静下来,我只想歌唱,哪怕没有一个字可以唱给她们听,我也想歌唱。”①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女诗人不再简单地把男性视为女性不幸的根源。诗人意识到,这一不幸的根源有更为深远的历史的、意识的、制度的、现实的原因。更重要的,她意识到从一种敌视的、仇恨的情感不能引出任何积极的成果——幸福,女性的幸福和男性的幸福,只有建基于爱的基础上。说到底,那种抱怨的、愤怒的、仇恨的情感,在把男性恶魔化的同时,也把女性自身贬低为恶的渊薮,在吞噬对手的同时,也在吞噬自身。在《一个人的对话》中,诗人写道:“你是否使用了眼睛,/让男人来到世界,骗取他们的爱?//我因为惊奇,张开眼睛,/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到来,/露出白色的肋骨和闪光的皮肤,/美和善行有了新的形式,/我闻到与自己不同的气味。/他们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我的影子,/他们都在哆嗦,失去了知觉。”在这里,男性被视为“美”和“善”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剥夺性、侵略性的异己力量。归根结底,女性的幸福和男性的幸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性之间的问题不应该是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它实际上是一个能否爱、如何爱的问题。如果以战争的眼光来看待两性问题,则这场战争难免旷日持久、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只有改变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两性关系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改善,或者说建立起这一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另一个艰难的意识转变。基于此,池凌云对所谓女性意识也多有反省。在写于2004年的《我注视过她的眼睛》中,诗人一方面同情于女性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对“反叛”的合理性及其后果表示怀疑,认为它只是加速生命的焚烧(“众多姐妹中的一个,体弱多病/我听到她呼痛/血液在皮肤下受阻/反叛的红药水加速了暗中的焚烧/她抚摸身体上无法褪去的瘀青/‘这是昨天留下的’”)。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委婉地批评了这种盲目的反叛,称之为“迷途”:“我记得夜色中的鸽子仍是只聪明的鸟儿/可现在她们不再认得归途”。池凌云关于“仙女和天使是一对姐妹”的说法,同样包含深意。仙女和天使代表了诗人的人性理想,这一理想在第二代女诗人那里曾经遭到广泛质疑,但在池凌云身上,它并未失去吸引力。仙女是东方的,天使则来自西方,但她们都诞生于人性的需要。诗人试图在共同的人性的基础上,把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姐妹结合为一个爱的家族。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诗人认为诗歌的技艺就是爱和怜悯:“‘你如果歌唱,你的技艺需呈银白色,/对生长的树给予怜悯。’//是啊,所有的树都铺成闪光的阶梯,/我的歌谣唱到天使,/她们穿着美丽的长裙,/眼神柔和,就坐在穷人身边,/月亮映照他们银色的汤匙。”(《一个人的对话》)。与第二代女诗人普遍的绝望心态不同,池凌云也没有放弃对未来和幸福的希望。尽管她告诫年轻的姐妹“这是幻想,/我要她发誓不要显露口音,不能歌唱”,但她仍然坚信生活是值得的,也不缺乏希望:“她就要伤心了,然而她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天,/会飞走,会有自己新的发明。”(同上)。这种在苦难的阴影下对爱和希望的虔敬和坚执,正是池凌云诗歌中最为感人的东西。
池凌云是少数几个让我产生敬意的当代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诗之永恒就如爱之永恒,可以在顷刻间被感知,无须等待时间的检验。”①从池凌云的诗中,我相信自己感到了这种永恒,并且在它们的撞击下受到了弗罗斯特所说的“永远都没法治愈的创伤” ②。我承认,正是这种被击伤的感觉,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冗长的文章。
2010.1.20-2.25
① 本文所引池凌云诗均出诗人的两本诗集《一个人的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池凌云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诗人的第一本诗集《飞奔的雪花》我没有见到。
① 扬·乌拉夫·于连.哦,现实:安娜·吕德斯泰德诗歌中围绕一个母题中的编织物.// 在世上做安娜:安娜·吕德斯泰德诗选.杨蕾娜,罗多弼,万之,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81.
① 池凌云《为谁写作》,见池凌云博客http://www.sina.com.cn/s/blog_489e5250010085bs.html
① (德)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梁晶晶,译.台北:倾向出版社,2009:130.
② 池凌云《为谁写作》,见池凌云博客http://www.sina.com.cn/s/blog_489e5250010085bs.html
①池凌云《为谁写作》,见池凌云博客http://www.sina.com.cn/s/blog_489e5250010085bs.html
①见《池凌云诗选》封底说明。
①见《池凌云诗选》封底说明。
①见《池凌云诗选》封底说明。
①② 弗罗斯特.艾米·洛威尔的诗.//弗罗斯特集.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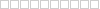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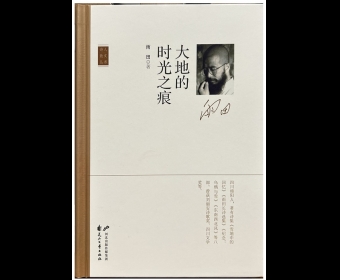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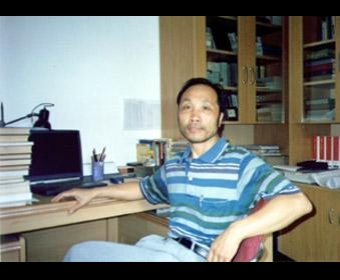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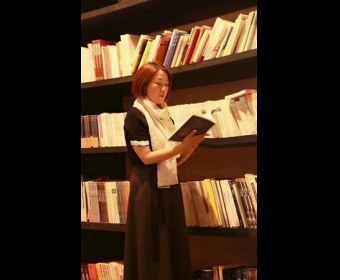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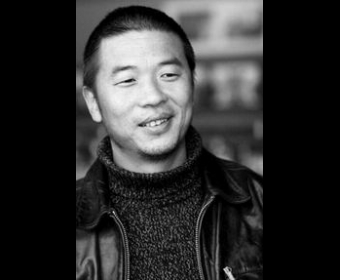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