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池凌云是一个对存在的黑暗有着深刻体察的诗人。在池凌云的诗中,从一开始就凸现着一种强烈的黑暗意识。她早期的诗《黑甩动长长的辫子》已经表现出对生存之黑暗的异常的敏感:“黑有条长长的鞭子/从你的手中甩出/……/我说出了一切/却无法说出这些年鞭挞我的黑暗/……/她有自己温暖的舌头和脉管/汲取黑珍珠刚刚开启的初吻/比白色更加纯洁/清晰的黑,让一朵不安的火焰/回到最初的睡眠”。在池凌云的诗中,到处散布着、弥漫着黑暗的粒子,它们出现的密度和尖锐的性质足以令读者惊心:
光的内部贮藏颤动的黑暗/一颗颗黑色的粒子环绕我的手臂/像一个城市在枯竭中燃烧。(《旧城·第十巷》)
而关节的缝隙正接受黑暗的研磨/它们互相抵抗,挤压/一些尖锐的东西逐渐平坦。(《按摩椅》)
没有一个人可以紧紧抓住我们/阻止我们在黑暗中一点点消失(《今天,谁来给我们讲故事》)
黑的卓越与合理性,完美的运动/覆盖所有感官。从隐秘的窄门/粘稠的油膏流出黑夜/月亮和星河,缩小的宇宙。(《午后》)
你的双眼埋藏着一个冰窖/正午的太阳都无法把她填满(《盲》)
黑夜曾给它们喝下黑色的汁液/使它们无法健康地活下去(《安慰》)
你满足了那朵漆黑的花/喂它所有光,让它胜利(《你日食》)
你背对缺席的婚礼,依然无法阻止/倾倒过来的黑暗(《肃静的门廊》)
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诗人的内心常为黑暗所包围。在当代诗人中,对于存在的黑暗、寒冷有如此彻骨体会的诗人并不多。池凌云诗中的这一黑暗意识,当然与频繁光顾诗人的苦难体验有重大瓜葛,但其尖锐和沉痛之处又超出于具体的苦难之上——它们一方面是对于人性本身之黑暗的体认,另一方面也是对时代之黑暗的体认。人性的黑暗源于愚昧、自私、怯懦,导致爱的匮乏和丧失。时代的黑暗更具体、更琐碎,然而也更揪心,它在空间上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把我们的分分秒秒都卷入到它暴力而无情的齿轮中:“机械的力禁锢了双脚/……/而关节的缝隙正接受黑暗的研磨”(《按摩椅》)。或者如诗人笔下的钉子,把我们“牢牢固定在单调的节拍”,“看我们氧化,收获看不见的洞”(《钉子》)。当我们拥有一切交通的便利,我们却失去了交流的愿望和理解的能力,成了一枚“在钢铁的硬壳里弄空自己”的钉子。尤为讽刺的是,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对螺丝钉的理论报以轻蔑的时候,我们自己恰恰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我们的自由就是以钉子的方式拥有“几寸锈蚀的记忆”,以“造成短促人生的复杂结构”。当我们忙于在天上飞来飞去,在电视里进进出出的时候,也许我们恰好把我们的自由出让给了技术和制度的魔鬼。池凌云的诗呈现了这一交易中黑暗的一面。正是在这个层面,池凌云的诗呈现了一种复杂的时代性,它总是在具体的、触及当下生存的情景中展示自己精确的诗艺,因而也不缺乏中国性。尽管诗人关心永恒,但它并不那种直奔永恒的诗,也绝不在假设的永恒的自然里陶然忘怀——池凌云的自然诗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的因素,掺入了诗人对当下处境的关怀以至某种焦虑不安。池凌云诗中的这种黑暗意识也与19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中所谓的“黑夜意识”相当不同。“黑夜意识”主要指向女性的生存体验,池凌云诗中的黑暗意识则指向更为广阔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讨论,这里暂不展开。
然而,苦难也孕育着拯救,就像黑暗的中心孕育着光明,木头的中心怀抱着火。在池凌云的生活中,诗歌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代表光明的拯救力量出现的。“所有堕落的灵魂都是因为期待光明太久/只能选择黑暗作为故乡”(《我无语时受到的灼烧比说出来还多》)——这里对“堕落的灵魂”所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充分体现了诗的人道的力量。这是源于爱和理解的力量,也就是诗的光明的力量。如果说诗人有着强烈的黑暗意识,那么也可以说,诗人也有着同样强烈的光明意识。事实上,她的内心常是黑暗意识和光明意识辩难、争持、对决的战场。黑暗意识和光明意识的对峙,造成了池凌云诗歌内在的紧张,也成为其诗歌主题发展的动力。诗人告诫她的孩子:“你要学会远离光也能生活”(《这是拖着灰发辫的冬天》)。远离光又怎能生活?那就是让自己成为光源。诗人不得不“选择黑暗作为故乡”,以至自居于“黑暗的中心”,但在其内心深处从未放弃对光明的期待:“它占据了黑暗的中心/它要走出去,抛开所见之物”(《灯的皇冠》)。但是,如果世上本没有光明,苦难的人类怎么办呢?诗人的回答是,燃烧。她说:“这么多技艺,我只学会一样:/燃烧”《夏天笔记》),“在黑暗中燃烧/流出明丽的形象”(《双重生活》),“呼啸着燃烧,也不会发光。”(《沙尘暴》)诗歌的人性之光,就是燃烧所诞生的“一点点消耗你的艰难的光”(《玛丽娜在深夜写诗》)。她也呼唤读者和自己一起燃烧:“谁与我一起燃烧?”(《木房子在梦中着火》)
一切愿意奉献于价值创造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燃烧。但我们历来的信仰却相反:生命的意义在苟存。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观,每个人的选择决定了他是成为光明还是黑暗的一部分——你不是成为光明的一部分,就是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期间供我们犹豫的空间是狭小的。至于我们的诗人,为了成为光明,是不惜将自己化为灰烬的。池凌云诗中反复出现的灰、灰烬的形象实际上隐喻了这一成为光明的过程。灰和灰烬乃是燃烧和光明的纪念:“灰烬的灰/绕过暝色四合的长廊/一座无穷无尽的塔在向上延伸”(《无尽塔》),“你的黑灰不再炫耀火/而灼烧和死寂都是我们的天赋/我只想走向那未知的疆域/扒开每一颗黑色的种子/看它怎么在每一个白昼活下去。”(《你日食》)在池凌云的诗中,“燃烧”、“灼烧”、“火焰”、“灰烬”是与“黑暗”对称的另一类关键词。正是它们为无尽的苦难和黑暗带来了救赎。
因此,诗人给予那些以自身的燃烧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的生命以无限敬意。《圣雄甘地》和《安息日》是献给两位成为光明的牺牲者——甘地和林昭的沉甸甸的作品。“仅有一根竹竿的人,诚实是唯一的武器/以为无私的爱可以唤起人类的本性/——当敌人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只有真理和爱才能战胜。在你的墓前/活着的人们轻呼:哦,罗摩神啊!”——这是概括而准确的甘地的精神肖像。然而,“经由你所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自己的不公正”,受到甘地精神光芒照耀的也包括他的敌人。事实上,“不公正”无论对于施予者还是承受者都是黑暗。甘地因而同等地给予了“不公正”的施予者领受光明的机会。《安息日》写得更沉痛,也更尖锐。这一仍然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之禁忌的一部分的题材本身,就显示了诗人眼光的敏锐和关怀的深广。诗人以女性的同情切入林昭的悲剧命运:“请给戴两副镣铐的人取下一副/让她暂时离开小小的黑房间”,“请给她热水和白色衬衣/原来那件已经脏了,遮住了光线”,“请给她爱,让她成为母亲/冲着襁褓里的婴儿微笑”,“请给她丝质头巾,还她带露的早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院墙外那些感受奴役的人们快乐的舞蹈、欢呼,盲目的热情所筑起的高台。这种对比,把一个人的悲剧上升为民族的悲剧。“无休止的审讯让一个患病的健康/无数健康的人病倒,在共同的身体里循环”——这里,自由与奴役、健康与疾病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具有强烈反讽意义。英雄已经化身为光明,安息在草、木和永恒的时间里。然而,在祖国无边的疆域里,黑暗依然是思想的主宰,关于自由和爱的知识还是一个秘密。真是痛何如哉!
5
爱的受难大概是所有苦难中最个人、最刻骨铭心而又最具普遍意义的。在当代诗歌中,池凌云属于有意回避对爱情作正面描写的女诗人。相反,池凌云不遗余力地对情爱的阴暗面做了深入的表现——爱的丧失和缺席构成了池凌云诗歌的另一重大主题。这种对于情爱的黑暗体验构成了其黑暗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她说:“爱的运动/是残酷,是不断地丧失/就像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肖像》),“我看不见一段完整的爱”(《存在》)。那些对爱仍然抱有期望的人,似乎只能假装它的存在为自己打气:“我假装一切不是不复存在/爱,并没有被荒废/依然驱动我前往陌生的地方。”(《我假装喜欢鲜花》)诗人在爱中看到的是不是坚守和忠贞,而是遗忘和背叛。《那一年七夕》、《不曾相识》、《读一个人的回忆录》等诗都以爱的遗忘为主题。《那一年七夕》叙述一个人失爱的痛苦以及这痛苦的迅速遗忘,随后的加速的爱和加速的遗忘。最后只剩下那个一直设法安慰失败恋人的叙述者对这爱的变形记惊诧不已:“只有我还记得曾有申诉者的痛苦银河/……/而今天,如果必须有人想起一些什么/那也是从记忆到遗忘的过渡/关于七夕,确实没有什么好纪念的”。《不曾相识》写时过境迁后恋人之间的陌生:“经过这么多年/你的梦比你更记得往事/我从未想过你的泪是假的/你长途跋涉的喜悦是假的/可是你却装作不认识我/这是我们终生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虽然试图安慰自己,“或许你只是胆怯了/……/我还是相信/你在进食时的悲哀/你虽然不看我,却在心里想我/你极力逃避,却又想见我”,但终于还是明白了:“誓约的一部分就是谎言”。她由此总结出的爱情纲领是:“只爱陌生人。”类似的悲剧几乎是恋爱的常则,鲁迅的《伤逝》对此已有深刻表现。爱情不但需要细心呵护,而且需要随时更新、成长,更为苛刻的是,需要双方同步地更新、成长。也就是说,双方只有始终保持同频共振,爱情的动力才能维持不衰。如此苛刻的条件几乎就是让爱情成为一桩不可能的事业。所以,聂鲁达说:“爱很短,遗忘很长。”《读一个人的回忆录》针对莎乐美的情感经历进行评论,表达的却是评论者在爱情中体验到的荒谬和空虚:“爱与性有时如此难以分辨/当每一次结合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你忘记了这也是与永恒空虚的子宫调情/……/一切爱都伴随着荒谬。没有什么可以不朽”。人们为了躲避空虚而逃进爱情(“与永恒空虚的子宫调情”),爱情的不可能又使人们陷入荒谬。事实上,爱情的不可能是人性必须面对的深渊之一,并以其切肤之痛最醒目地昭示了存在的黑暗。
与爱的不可能主题平行发展的则是孤独的主题:
一个被遗忘的人开始透露自己的身世/他举起一只空杯子告别,最终却无处可去(《微醉》)
所有人都只是单独的一个/然而,总有人在等他/从门口走进来,坐在空位置上。/这是唯一能与我们一起悲伤的人/他搓着双手,惋惜过早醒来的梦/看到我们渐渐老去的父母/再也无法把故事讲下去(《今天,谁来给我们讲故事》)
这个午后,她把双手晒了又晒/它们像两个走失的孤儿/互相抱紧,还觉得孤单太多。(《午后》)
经线压着纬线/互相契合,又处处隔离(《编织品》)
一生所有,只是孤单的身体/只是疲倦而苦涩的心(《在雾中》)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陌生人(《醉了的小提琴手》)
孤单的夜晚,我不写信/我只想抱住一棵树痛哭(《存在》)
这些诗里对孤独的体验可谓深入骨髓。《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写了一个从寻找爱、寻找理解到习惯孤独的过程:“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游戏啊——//我们曾轮番躲在衣柜里/不出声,不让别人找到我们/一切爱所需的训练:看谁的孤独更持久//后来,我们忘记了要去找到对方/习惯了默默无闻地生活/宛如躲在一个大箱子里。//然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来找我/我们早已是没有名字的失踪者。”孤独是爱的反面,也是人之定义的反面,它是从人退化为甲壳动物:“宛如躲在一个大箱子里。”当然,诚如诗人所说,孤独也是“一切爱所需的训练”,但是孤独一旦披上习惯的甲壳,人们就会用自私和冷漠来抵拒爱和理解,“忘记了要去找到对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把自己制造成了失踪者。由于同样的原因,那个“唯一能与我们一起悲伤的人”,“再也无法把故事讲下去”(《今天,谁来给我们讲故事》)。孤独也因此成了苦难的同盟,爱和幸福的对手。《发明一个亲爱的》是孤独者与一个不存在的爱人的对话:“发明一个亲爱的,即使只是一个/微小的人,我们可以告诉她/我们颠沛流离的一生,孤独的/一生,全是因为她/一个可以抱在怀里哭泣的人”。这样的诗只能是极端的孤独体验的产物。然而,诗人在诗末却话中有话地说:“对于你,除了我们/已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你没有别的机遇。你知道你是谁”。我想,诗人的意思是说,爱者与被爱者实际上是互相需要的,孤独者需要发明一个亲爱者,亲爱者也需要被发明或被发现。在真正的爱中,爱者与被爱者也是统一的,你/我既是爱者,也是被爱者。由此可见,诗人实际上从未放弃对爱的追寻。即使此身不在,你/我化身为小瓷像,爱者与被爱者依然渴望相认:“假如有人认出我,轻轻拍动瓷像/我会颤抖着说:是的,是我”(《我假装喜欢鲜花》);即使置身地狱,那颗爱人的心依然鲜红如初,渴望安放:“弯曲,弯曲,黏土与蛛网/是不再防御的脊柱/他依然爱着那颗鲜红的心/却因无处安放而哭泣/但他没有一张可供辨认的脸/铁钩锁住早已消失的唇”(《地狱图》)。诗人一边悲悼“所有死亡都源于爱的死亡”,一边却坚执地认定“所有旋律,都在追随爱着的灵魂”(《遗失的旋律》)。她说:“多年前的爱情对一生也已足够”(《旧城·遗忘之巷》),“除了无法阐明的爱/窗外摇曳的树,我们一无所有。”(《苦恼之夜》)池凌云无疑是一个悲观然而坚定的爱的守望者。这样的守望者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越来越少了。
在池凌云的诗中,从爱的丧失中发展而来的遗忘主题有一个普遍化和不断深入的过程,值得我们加以进一步分析。当诗人对于遗忘的考察从情爱领域逐渐向人们普遍的生存状态延展,她惊异地发现人之善忘不仅表现在爱情中,也表现在苦难人生的一切方面:
我们一直承受着灾难,却早已忘记/有多少人死于灾害(《发明一个亲爱的》)
我听见颂扬之声。当我记录/只写下禁止和空白/河流的洞察,无声而缓慢/干涸与爱,遗忘与爱/这多么符合我们的本性(《树或者河流》)
所有疼痛都会被遗忘(《纪念一个死去的女人》)
我正在遗忘刚刚经历的灾难(《经历》)
所有路过的人,都弹着遗忘的琴(《时空维度》)
或者,我也将忘记我是谁/像探望一个老朋友那样回忆自己/某个难以度过的日子,难以忘怀的人/都不再重要(《在夏天改写一首冬天的诗》)
遗忘,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日常状态。无论对个人的疼痛还是集体的灾难,人们逃向遗忘,恨不得以罪犯逃离现场的速度,不怕更快,只怕不够快。为了更快遗忘,人们想方设法把疼痛和灾难非现实化,而庆幸“纠缠在梦中的一切都已消失”(《九月八日》),或者干脆“沉入深深的睡眠”(《沉入深深的睡眠》)。为了安全地活着,也是为了摆脱心灵的重负,人们有时甚至主动求助于麻醉术:“一定要使用麻醉术,大夫/即使只是暂时的欺骗/即使一些病痛永远无法治愈/你要让她相信/日复一日,多少人依靠麻醉术/继续活了下来”(《麻醉术》),“这是一种新的处世态度/在确凿的光线中,像是另一个人的血液/流向别处。我丧失,却像在增多//这就是她的魔术,通向自由心灵的/道路,仍然畅通。碎掉的只是齑粉/一半现实竖立在我们中间//只需要今天,不要往昔/迟缓中的遗失就像是一次日落/走掉的歌谣透过一扇厚重的门回响”(《迷醉心灵自由的麻醉师》)。诗人指出,借助麻醉和遗忘得到的“心灵自由”,只能让我们得到一半的现实,失掉的却是救赎的机会。这所谓的“心灵自由” 的实质是逃避责任和承担,是心理的怯懦和思想的缺席。这样做的后果乃是美化和加强了心灵对苦难的依附状态,同时因为放弃未来而放大了苦难的力量。“我们一直承受着灾害,却早已忘记/有多少人死于灾害”(《发明一个亲爱的》)——正是因为对灾难的遗忘,“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并没有互相拯救”(《经历》)。事实上,遗忘是一个不断下沉的时间,而且拒绝“一切诗意的召唤”(《沉入深深的睡眠》)。诗人期望有人从这样的时刻“抬起头,像一个沉重的磨轮/转动,呼喊,……获得自由”。她说:“我将与她一起醒来。”(同上)这是诗人对对读者的邀请——因为诗人其实一直醒着,替我们在这艰难的时代的暗夜里守夜,等待着她的读者。
由此可见,诗人虽然对爱的丧失、对孤独和遗忘有锥心的体验,但她从未放弃对理解的寻求和希望。在对苦难的敏感上,池凌云与“完完全全从苦难中获得灵感”(保罗·奥斯特语)的诗人保罗·策兰存在可以类比的地方,但与策兰对理解的绝望(“自称为‘无人’,然后给那些在精神上剥夺其作者身份的人写信,就如同在真空中进行言说,说出的话永远不会进入对方的耳朵”①)不同,池凌云的诗始终是为理解而写。在一篇题为《为谁写作》的札记中,诗人写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亲爱的读者’是单数,第二人称,是一个‘你’。作家写作不仅仅是要解决自己的困境,而是因为‘你’”,“为‘你’写作……她的曲折困顿,她经历的种种危险,你早已帮她承担。就像是一个拆开信件的人,在那一刻,它并不是落入别人的手中,只跟‘你’有关,是‘你’赢得她的芳心”,“她崇拜‘你’,她觉得应该把一切都交给‘你’”。②基于这种对理解的坚执,池凌云的诗无不包含着对“你”的热切期待,而且总是在与“你”的对话中展开和发展诗的主题。由此,池凌云把诗歌变成立一门精湛的对话艺术。对话,在池凌云是作为对爱的丧失、对孤独和遗忘的反抗被引进到诗中的。诗人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一个人的对话》,从中不难看出诗人的深意。然而,这一对话又被认为是属于“一个人”的,因而又具有某种虚拟的、否定自身的性质:它一方面表明诗人深知在走向理解的途中存在的重重障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诗人其实饱受孤独之苦。在那首诗集借为题名的诗中,这一虚拟的对话既可以看作诗人与自我的对话、诗人与诗的对话,也可以看作诗人与某个理想读者之间的对话——这一理想读者在这里被明确界定为一个女性。这一对话主题在《池凌云诗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而其虚拟的方式也被沿用——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属于孤独者的典型方式。《发明一个亲爱的》、《你是有罪的》、《阳台》是诗人与虚拟爱人的对话。诗人虽然声称“你并不存在”,而且把自己对爱的期待说成是“给自己喂下毒,不辨是非”(这也是所谓“有罪”的内涵之一),但她仍然随时准备为奔赴理解而“出发”,即使“这最后一击可以让我碎掉”(《你是有罪的》)。《阳台》表现了诗人对与自己一样“震惊于黑暗”的同道者的惺惺相惜之情,也是对理解的直接呼唤:“从他内心升起的苦闷哼唱/被我接纳。……//而他的每一扇窗户都对着我/每一次咀嚼都在掏空我/他的嘴巴是一个大写的字母C/他乐于造成我的命运。”诗人把同道者之间的这种理解视为“一次暗中的飞翔”,将“带我进入没有强烈硫磺味的居所”(“硫磺味”暗示了现实的地狱性质),从而“获得片刻自由”。《寄信石家庄》、《与Z说西藏》、《在瑶溪,想起一位友人》、《卵球,一种态度》、《遗失的旋律》、《谈论银河让我们变得晦暗》是朋友之间的直接交谈;《游船》、《苦恼之夜》、《玛丽娜在深夜写诗》、《所有火焰和黑暗,所有深坑》、《我今天只读两首诗》是诗人与希姆博尔斯卡、茨维塔耶娃、卡瓦菲斯这些精神上的同道之间的对话——这两类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诗人亲切动人、魅力四射的语调,这一语调的特征则揭橥了对话的深入程度。还有一些诗则可以看作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谈》昭示了诗人与读者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诗人所付出的,正是读者所收获的,另一方面读者也是造就诗人的人。《留下》则可以看作诗人留给未来的诗学遗嘱,或者对读者参与诗歌对话的邀请。尽管诗人对于对话的可能有所保留(“房子等不到它的主人,/他们来了一群,又走了一群”),但重要的是始终对理解和对话心怀期待。这期待是关于诗的,也是关于未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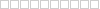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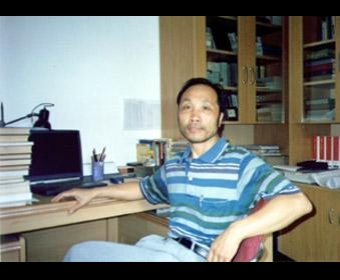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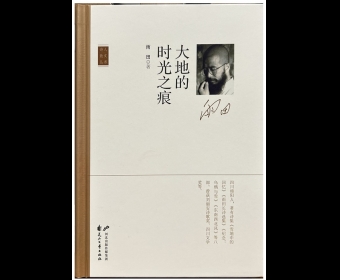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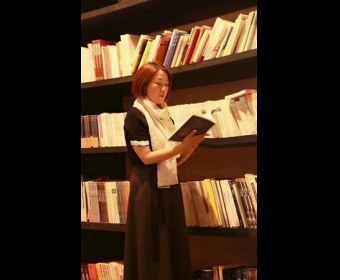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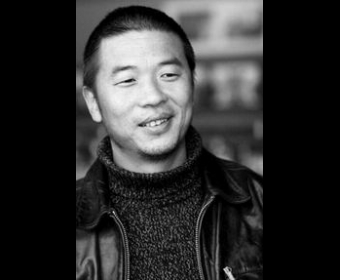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