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池凌云的诗中,还有一个重要系列的诗是以诗歌本身为主题的。在这些诗中,诗人对诗与语言、诗与现实的关系,诗和语言的可能与不可能,诗人的职守,诗的作用和意义等诗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我们上一节讨论的对话主题其实已经涉及池凌云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节我们继续对池凌云诗学中的其他部分开展讨论。《语言与我》一篇可以看作诗人的诗学总纲。正如前文指出的,诗人认为写作的目的就在抵抗沉默,为生活和苦难作证:“我抓住一个人说话,是为了阻止/沉默的树脂封住我的嘴巴”。同时诗人却又对言说的可能、语言表现现实的可能充满怀疑:“我能怎样说出我的困境?/词语不像我想的那样/被我亲近……/我以前所做的/只是一次次对着它的后脑勺叫喊。”然而诗人同时深知,一旦放弃言说,就意味着屈从于空虚的日子,屈从于坚硬、冰冷的现实:“给夜涂上颜料/再从起皱的旭日,把一个火球掏空”。“为此,我将继续写下一个个词语/让它看着我一边嘲弄自己,一边哭泣着消失”——诗人一直在绝望中坚守,绝望然而绝不妥协。这一主题在《谁也不敢在黑暗中独自说话》得到忠实的回应:“坦率和勇气都不能/作为此刻你长久不变的证明,/如果你决定用一生守护它们/你先要在黑暗中保持沉默,想明白/是不是真的要让某些事情发生/你是独自抑制黑暗的人/你为你将要说出的一切而活”。“你是独自抑制黑暗的人/你为你将要说出的一切而活”,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两行诗句更能说明诗人工作的性质了:诗把现实从沉默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为理解和对话创造了可能,由此在时代的暗夜中引进了一线星星之光,并以此守护“坦率和勇气”。《我曾这样写下文字》在诗人与诗之间展开对话。诗人作为诗的书写者,似乎是诗的主人,实际上诗一旦完成,就脱离了诗人的掌握,它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它和读者之间的遭际:“不同的人,造成你命运的千差万别”。在这首诗里,诗人对诗与现实的关系表达了一种相当乐观的看法:“你说‘出航’,让出海的生命充满了危险/你说‘归来’,无数悲痛的离别之人/再次获得重逢。”词在这里直接变成了现实。在另一处诗人表达了词与诗人的亲密关系:“我熟知它们的命运/就像词,知道我的命运”(《自然元素》)。但在多数情况下,诗人并非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所有细节中》是另一首对诗与现实的关系进行思考的诗:“冰在融化,越来越少的词/在分裂。水和鱼/互相辨认缺氧的现实”。词试图通过自身的分裂、成长融化现实的坚冰,但诗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现实的本质——缺氧的现实决定了诗的缺氧状态,也决定了语言的缺氧状态。水和鱼在这里既是诗与现实关系的象征,也是诗人和语言关系的象征。时间(现实的千面之一)在这里被视为“有毒的汁液”,它不断回收开过的花朵,但诗人的事业就是冒险把它们从流逝中赎回:“但它们必须回到大地/在石头内部,炙热的晶体在成长”。然而,诗人并没有从这里通向一个廉价的乐观的结论。她接着说:“从一张折叠过的纸/从一个变小的句号,我来。你采下/它们,用枯萎的手/让收藏多年的黑发变灰。”显然,诗人认为诗的艺术并不能让美永葆光彩,通过诗歌之易于枯萎的手,我们只能采摘到黑发变灰的二手的美。这里,诗人对诗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信赖诗歌的救赎力量(正是这一信念给予她在苦难中坚守的勇气,因此这一信念与其生存的本质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她又深知这一力量的局限和在现实面前的无力。诚如晚年奥登所说,“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诗既不能改变人们受难的事实,甚至也不能给受难者恰当的安慰,由此导致诗人对诗的作用和意义的怀疑。这好像是诗人的动摇,但恰恰是这动摇让我看到了诗人的仁心与大爱。正如前文所说的,池凌云从来不是一个为诗而诗的诗人。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诗人,她要求她的诗拥有一种温度(而不是体面的风度),能给苦难的人带去温暖。在另一首诗中,诗人写道:“微小的笔负担着寂寞和创伤/空无一人的道路在伸展/只有它们能理解,带刺的雨/玷污了最好的墨色”(《存在》)。对池凌云而言,诗歌是勇敢的承担,这承担既包括生命的寂寞和创伤,也包括自身的“空无一人的道路”,还包括现实“带刺的雨”对“最好的墨色”的玷污、涂改、擦洗。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说出一个弱小的词,给予怜悯/给予爱”(《九月八日》),并经由怜悯和爱的启示体会到“那让我疼痛的,也在疼痛。/那让我破裂的,自己早已破裂”(《树或者河流》)。这是心的力量,是有能力“使一颗石子变软的力量”(《不是火灾,是深渊》)。按照悲观论者的看法,包裹我们的皮肤就是我们的边界。但是依靠爱和怜悯的力量,诗歌最终得以越出这孤独自我的边界,战胜遗忘,走向人群,走向理解,走进人心。
池凌云不但是一个忠实于生活的诗人,更是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诗人。忠实于内心,忠实于个体生命的体验,这可以视为其诗学的根基。如果诗歌对池凌云来说是一种内心生活,那么写作对她就是一个剥开自己、剥开灵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歌除下了自我的日常表象,而得以深入到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名望甚至没有知识的内在的、本真的自我。这就是池凌云的体验诗学的根本要义。她说:“关于任何作品,唯一该问的问题是——‘它是活,还是死?’”,活的诗“不仅能诉说,还能倾听,甚至能伸出手,握住你的手”。①诗之活需要诗人用自己的内在生命为它供给血液和温度。因此,诗的写作实际上意味着内在生命的额外支出与损耗:“最深处的琴弦消磨我/我的血液绚丽缤纷”(《醉了的小提琴手》)。忠于存在的高昂代价是用血液支付的。《茧》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达到了令人震撼的效果:“安抚从内部开始,/凭着深处的柔软,你到达。/……/一颗从未到达过的小心脏。/不知自己是什么/它抽雪白的丝/向着沸腾的水,挺立/剥开自己。” “茧”的意义不在于把自己紧裹起来,躲进“仿佛没有寒冷”的“最后的安全地带”,而在于打开自己,变成丝(诗),给世界带去珍贵的、稀有的温暖:“当世界整个变成金属,/一头蚕,变成琉璃糖/把自己打开”。忠于自身生命的写作就这样在沸水里献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诗人既把自己深处的柔软暴露给世界,也就失去了任何保护,处于世界上最不利、最无助的地位。在这一地位上,只有读者能够保护诗人。正确的、充满善意和理解的阅读保护了诗,也保护了诗人,而错误的、粗暴的、歪曲的阅读就是对诗和诗人的侵害。这就是诗人为什么依赖读者的原因。保罗·策兰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种粗暴的阅读所谋害。诗坛对于池凌云诗歌的长期漠视也是对诗人和诗的一种蓄意伤害。诗人对此深有体会地说:“美是万事中最难的事”(《盲》)。
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池凌云在其诗作和诗学随笔中还提出了若干独特的、与上述体验诗学密切联系的诗学命题,其中有三个命题特别引起我个人的共鸣,它们是:无知、无名与饥饿。长期以来,池凌云有意让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她说:“我至今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除了生命的渺小。时间飞逝”(《与Z说西藏》),“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炫目的亮光//这世上有形的一切/你并不认识它们”(《盲》)。她甚至宣称自己“一无所知”:“我对黎明的色彩一无所知/可火红的炭火一直在内心喧腾/死去的贫穷的囚徒啊,那把铲子/只是一个梦,挖开是另一个梦/露出金属的指针和刀柄是谎言/是命运设下的又一个骗局:/鲜红的色彩使夜晚变得明亮/一把奇妙的匕首的全新的涂鸦”(《一无所知》)。在这里,“铲子”是被现代人奉为上帝的理性的象征。在信奉理性的人们眼中,它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诗人却宣称它“只是一个梦”,而人们依赖理性认识世界的愿望则是“另一个梦”,由此获得的知识只是“谎言”和“骗局”。显然,诗人认为理性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的物质性的一面,但它并无助于心灵对黎明的色彩的感知,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内心喧腾的炭火的正确知识。与此相关,理性(“铲子”和“匕首”)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狂妄的,因狂妄而固步自封的。这种态度,正如里尔克所写的:“我怕人的聪明,人的讥诮/过去和未来他们一概知道;/没有哪座山再令他们感觉神奇,/他们的花园和田庄紧挨着上帝”(里尔克《我如此地害怕人言》,杨武能译)。一经这样的知识触及,万物便“了无声息”,“它们毁了一切的一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无知”的态度,它是谦卑的,和开放的。借助于谦卑,借助于“不满”,“无知”向着人的全部存在,向着无限,向着巨大的神秘开放 。这样的“无知”也是走向理解的起点。正是通过保持心灵的“无知”状态,诗人赋予了她的诗一种开放的、理解的力量,这一力量构成了池凌云诗歌完整的、贯穿始终的结构支撑。
“无名”是诗人第二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写于2004年的《白色中的黑色》第一次提出了要从诗作中“擦掉我的名字”:“我厌弃了这些在黑夜中写下的文字/它们曾与谎言并排放在一起/得到的耻辱比荣誉更多/我要在天亮之前/擦掉我的名字,与它们分开”。表面上看来,诗人要与自己的作品分开是因为“它们曾与谎言并排放在一起/得到的耻辱比荣誉更多”,但内在的原因是因为诗人认识到艺术的本质是“无名”的。在同一首诗中,诗人还写道:“我只依靠默不作声的树/与消隐的生命交谈/路过的人谁也看不见我”。2009年的《雕刻者》进一步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发挥:“她诞生了,得到火的允诺/四肢运动协调,却无处可去/那个胸膛像竖琴的雕刻者/早已隐匿在另一块无名的大理石中”。这里诞生的、被赋予名字的是“雕刻”,而“雕刻者”在“雕刻”诞生以后就从作品隐匿了,退出了。就诗学意义而言,“无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关联着诗歌写作的心理机制。“无名”在这里意味着诗人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无名者”奉献于诗歌之前,创作被视为一种自我的让渡和献出,而不是占有。在这一认识中,重要的是诗被认为是高于诗人的,诗人只是那无数献身于诗的劳动者中的一员。重要的,无限重要的是诗,那具体的和总体的诗,完成的和未完成的诗。第二层含义联系着诗歌的阅读机制。基于“无名”的信念,诗人拒绝将诗篇据为己有,而只是作为一件被献出的礼物交给理解的,也就是阅读的过程。因此,“无名”也意味着诗歌作为纯洁的礼物被献给了同样的“无名者”。这样,诗歌就成为一曲由无名献给无名的理解之歌。正是基于这样的诗学信念,池凌云把她的第三本诗集的后记题名为“遥寄无名”。上述“无名”和“无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坚守着一种低头进献的谦卑姿态,同时因这谦卑而向着无限之物和神秘之物开放。
“饥饿”是池凌云另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尼采曾说,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主要取决于创造它的是饥饿还是过剩。池凌云对此深有体会。她说:“事物因饥饿而存在,生命因饥渴而充满渴望。在饥饿中活着,这样的灵魂是轻盈的,适合与万物和睦相处。是饥饿使精神得以更新和延续,这一切就像在说:真正的言说之力——是无声,是对一切饥饿之源的真诚和无私的爱”。①在诗人看来,出于饥饿的写作才能成为有尊严的写作,出于过剩的写作只能流于消遣。但是我们随处见到的写作都是过剩的产物,出于饥饿的写作在当代诗歌中少之又少。在《池凌云诗选》后记中,诗人引西蒙娜·薇依的话说:“若无辛劳,若无源于辛劳的饥和渴,任何同民众相关的诗歌都是不真实的。”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池凌云的诗歌正是那种源于“辛劳的饥和渴”而与民众相通的诗歌。诗人从自己的饥饿和黑暗时分出发,终而理解了民众的饥饿与黑暗,也理解了存在本身的饥饿与黑暗。
在池凌云的上述诗学命题里,透露着诗人对于诗歌的一种独有的虔敬意识。我认为正是这一意识把她和大部分当代诗人区别开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孤独而醒目的存在。这种虔敬在海子、骆一禾、戈麦、昌耀相继去世以后,当代诗歌中已经趋于绝迹。诗歌的轻佻化、游戏化成为时髦,固有的功利化愈益变本加厉——诗歌的马车便一意孤行地在名利的康庄大道上奔驰。池凌云选择的却是一条泥泞的、充满艰辛的道路。但也许泥泞和艰辛才是诗歌的正道,而人人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也许恰恰是歧途。池凌云以她特有的对诗歌,对爱和幸福的虔诚,为我们构筑了当代诗歌的另类风景。
7
在当代女性诗歌中,池凌云的诗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辨识其意义的标识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把舒婷、傅天琳等视为中国当代第一代诗学意义上的女诗人,翟永明、伊蕾、海男、张真、虹影、唐亚平、陆忆敏等为继之而起的第二代女诗人,那么池凌云、周瓒、沈木槿、金铃子、宇向等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诗人就属于更新一代的女诗人。与第一和第二代女性诗人相比,池凌云这一代女诗人并不以强烈的女性特征引人注目。她们进入诗歌的方式不是女性的,而是诗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它悄然改变了或者说重塑了当代女性诗歌的面貌。这一事实所蕴含的文学史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无论舒婷、傅天琳一辈女诗人,还是翟永明、伊蕾一代女诗人都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虽然这女性特征的表现相当不同。舒婷那一辈女诗人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远甚于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但这并不说明她们缺少性别意识的自觉,或者她们的作品缺少女性特征。这一辈女诗人的女性特征和女性意识并不表现于她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而表现于其诗歌的风格意识和美学特征。无论舒婷还是傅天琳,都有意识地强化了其诗歌风格的女性特征。这一以温柔、含蓄委婉为主要特征的风格意识既是其写作诗学的基础,在阅读层面上又是其美学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在一个缺乏温情、性别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的社会环境中,被刻意强化的女性温柔既是社会意识上的抗争,也是美学上的挑衅。它所引发的后果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一方面是来自官方的僵化美学的激烈的批判,一方面是来自年轻一代的热烈倾心。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舒婷对年轻一代读者不仅是活着的缪斯,也是爱情的教母——无论对男性读者还是对女性读者,都是如此。就像欧洲的浪漫小说教会包法利夫人向往爱情一样,舒婷的诗也是针对当时读者的一种情感教育, 让他们学会人的感情,学会爱一个人——舒婷诗歌的这一情感教育的功能恐怕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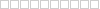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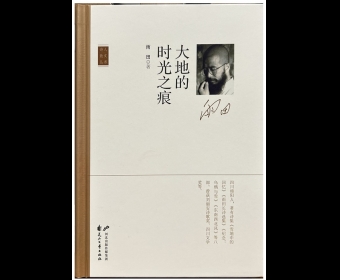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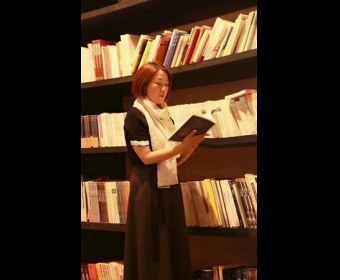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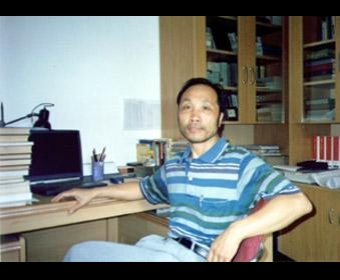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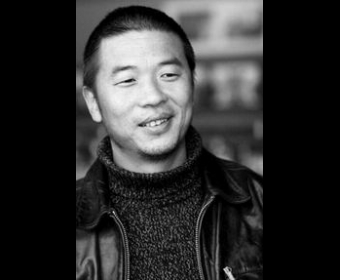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