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光,最终回到黑色的苍穹
我们寂寞而伤感,像两个木偶
缩在窘迫的外壳里
某一颗星星的冷,由我们来补足。
在大气层以下,我们的身影更黑
或许银河只是无法通行的游戏
看着像一个艰涩的嘲弄
它自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而如果我们相信,真有传说中的银河
这样的人间早已无可追忆。
宇宙的浩瀚与人类的渺小所构成的对比,给予我们强烈的震撼,但它并不是这首诗唯一的主题。与空间的茫无际涯相比,时间无限的广延更令人敬畏。这一切使诗中弥漫着一种宇宙性的荒凉,而同时却又贯穿着人和宇宙同一性的体验和信念。这是宇宙本身在说话,或者说是作为宇宙间一切现象的见证者的时间在说话,主体的存在和事物的存在在这里趋于一致。这首诗让我想起康德关于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伟大论断,以及陈子昂那首伟大的短诗《登幽州台歌》。它们都拥有一种非凡的力量,把宇宙的整体凝聚于精密的篇幅中。对于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时印证了上帝的存在。在池凌云的诗中,上帝似乎是缺席的,但是那宇宙性的荒凉本身却随时在召唤上帝的出场。康德理性的明澈和严峻,与池凌云感性的、诗意的“晦暗”似乎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两者同源于一种内在的洞悉。这样的诗歌不仅触到了心灵的边界,某种程度上也探及了宇宙的边界。我斗胆在此断言,池凌云于此已经写出堪称伟大的诗篇,可以和古往今来任何同等篇幅的杰作媲美。具有类似力量的诗在池凌云笔下还不止这一篇,《流水没有带走光芒》、《盲》、《在雾中》、《一无所知》、《无尽塔》、《春天的所有安排》、《时空维度》、《卵球,一种态度》都是同类的杰作。对我来说,这类作品标志了池凌云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不是那些处理时代处境和经验的诗篇。正是这类诗篇显示了池凌云诗歌真正的独特性所在。后一类诗篇,在我们的时代也许还有另外的诗人能够写出,而能够写出前一类诗歌的绝无第二个。
池凌云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感受性和缜密思维的结合——从以上诗例的分析中已可见出。在《游船》、《谈论银河让我们变得晦暗》这样的诗里,生动的感受性、想象的直觉穿透力和精密思维的结合,生下了堪称完美的诗篇。这一特点尤其彰显在池凌云对诗歌主题广延的拓展和深度的开掘上。此点将在下文继续展开分析,此处先行略过。
我说2004年是池凌云写作生涯中关键的一年,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池凌云一直不曾写出优秀的作品。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诗人已经写出了不少相当出色的作品,譬如《沉湎在绿树掩映的时光里》、《黑甩动长长的鞭子》、《对一朵野花的十种比喻》、《一秒钟归去来》、《一百棵乔木的树林》、《虹深处》、《布的舞蹈》等等,这些诗篇显示了诗人的才华,她那些后来引人注目的独特品质已然隐含其中。《黑甩动长长的鞭子》对于“黑”的发现,《布的舞蹈》对于“布”的意象以及它和女性命运的联系的发现,《一秒钟归去来》的速度感,《对一朵野花的十种比喻》、《沉湎在绿树掩映的时光里》、《一百棵乔木的树林》对自然的亲密体验,《虹深处》感觉的精敏,均表现出诗人心灵和诗艺的独到之处。但是,这些诗篇的重要性和2004年以后的作品还不能同日而语。这些诗篇的不够成熟之处,在写法上表现为没有完全摆脱朦胧诗的意象写法,因而难以展开复杂的经验过程。诗人试图通过组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例如,《布的舞蹈》,但也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在语调上多少还存在借用他人的倾向,例如《一百棵乔木的树林》酷似后期戴望舒的语调。诗人的心灵和个性也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和成熟。在2004年短短一年内,诗人一举解决了上述问题,成为一个在心灵和诗艺上同时一空依傍的诗人,不能不令人惊异。
3
池凌云的人生阅历中充满了艰辛和磨难。当她回顾幼年的经历,她说:“关于生活,我最早了解的一个词是‘贫穷’”(《池凌云诗选·后记》)。就在贫穷和孤独中成长,她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成年以后,苦难依然是诗人家中最殷勤的客人:“今天,我有许多悲伤/我数了一下,它们一共有四个/像坚硬的纽扣,紧紧靠在我胸前/走到哪里我都带着它们/一个人时就痛快地流泪”(《四分之三泪水》)。苦难的泪水仿佛流不完,也擦不完:“我在一尊佛像前忽然流泪/我不停地擦,还是擦不完”(《与Z说西藏》),“我不知道先擦干左脸/还是先擦干右脸”(《遗失的旋律》),“人多么小,多像一块哭泣的面团……”(《在蒙马特高地远眺》)。遥想的幸福没有如期来临,以致姐妹见面时,只能“一起悲泣没有来临的幸福”(《那时候我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池凌云的诗歌就从她本人这一艰难的人生经验中提炼主题,对其亲历的种种辛劳艰难加以文学的表现。苦难,孤独,爱的追寻、遗忘和失落,是池凌云频繁触及的诗歌主题,苦难更是其中压倒一切的母题,是其诗歌伸向存在之大地的繁茂的根系。
苦难是沉默的,而且总是倾向于孤单,因为愿意替苦难说话、与苦难成为朋友的人是少的。“风握住刀锋/刮开每一处湖中的明月/它唱着歌。/它只唱一个字,啊!/它反复唱,啊!”(《秋天,月亮将泡沫抹去》)苦难只能唱出“啊!啊!”这样粗野的、令听众生厌的歌声。千年百来人们一直在苦海中挣扎,但关于苦难的歌,我们又听到过多少呢?在杜甫以后,苦难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是默不做声的。仿佛就为了让她为苦难作证,把苦难从沉默中拯救出来,命运才不断地与诗人为难:“让她拥有母亲的慈悲/为正在受难的人疼痛”(《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雕刻者》)。诗人就是那个以抵抗沉默为使命,独自在黑暗中说话的人:“你是独自抑制黑暗的人,/你为你将要说出的一切而活”(《谁也不敢在黑暗中独自说话》)凌云也许是第一个基于主体体验而对苦难主题进行深入挖掘,并赋予诗意的尊严的当代女诗人。在当代诗歌中,当然也有别的女诗人触及苦难的主题,尤其对所谓女性的苦难的表现,曾经是一个相当时髦的话题。但是,这种苦难的表现很多时候仅仅是出于观念以至立场的需要,而缺乏深切的个人体验作保障。相反,在池凌云的诗歌中,女性的苦难总是与最深切的主体体验相联系,而且表现得那么节制,那么尊严,那么骄傲。是的,苦难也可以是骄傲的。她说:“唯有艰辛是纯洁的”(《偶然之城·在美和丑之间漂泊巷》),“她出众的悲伤/使她成为今晚的女皇”(《她流泪了》)。池凌云就是一个由悲伤为之加冕的诗歌皇后,是属于苦难中国的诗歌皇后,就像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属于俄罗斯,索德格朗属于芬兰,狄金森属于美国一样。在中国女诗人中,池凌云也许不是最广阔的,但她却是一个拥有一种顽强的内生力量的诗人,正是这种内在的力量赋予池凌云的诗呈现出一种少见的深邃。
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使得池凌云的诗拥有一种当代诗歌中少见的真实的品质。它有一种苦杏仁的味道,但也在苦涩之下掩藏着独特的甜味——它不是额外的装饰,不是多余的消遣,而是一味清热的药剂。诗对池凌云来说完全是生活的必须和疗救,对池凌云的读者来说也须同样如此。所以,池凌云的诗不是为生活的胜利者准备的,它是为生活的失败者而写。忠实于生活、以负责的态度执着于生活的读者将会在池凌云的诗中找到渴望的安慰,而那些踌躇满志、志得意满的人在池凌云的诗中会看见自身的空虚。在《一颗枣核有一千种智慧》中,池凌云写道:“我整天含着一颗枣核/为它掘一个温暖的墓穴/而它所能做的,就是讲述/短暂的甜,之后的无味。//一个无用的东西,我无法期望变幻/而它变得更加坚硬/我欲将断线从它内部穿过/而它拒绝。//夜色依然在黎明中滚动/棱角的创造补足言说之雪/一切图解忍受脱落。//没有什么可以扯碎它/它是今天唯一延续的东西/它不会觉得寂寞。”这首诗可以看作诗人的苦难诗学的宣言。“枣核”无用、无味,只有短暂的甜,但它真实、尖锐、坚硬、忠实于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扯碎它”,因而也是“今天唯一延续的东西”。
当然,在这样的诗学中也隐含着某种危险:当生活境遇发生变化以后,这样的写作——忠实于苦难的写作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活力的有效保持有赖于诗人应对两方面挑战的能力。一是在新的境遇下,诗人能否对苦难保持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敏感。很多在困苦中开始讴歌的诗人,往往在幸福中失语。这种情况说明诗人的写作仅仅基于自身的生活境遇,而对更为广泛的人类的饥饿状态缺乏敏感。这类诗人,随着自身的饥饿状态得到改善,其写作的动力难免渐告衰退以至枯竭。这是一个爱的广度的问题。二是诗人能否在新的境遇中更新原有的主题、题材、诗艺以至原有的诗学,开拓出新的写作可能。这可以说是一个爱的深度的问题。这些年来,池凌云在更新诗歌写作的题材,开拓新的主题,挖掘新的写作可能方面作出了可贵而有成效的努力——我们将在下文对此继续展开讨论。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自2004年以来写作上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了。上述两方面综合为一个爱的能力的问题。对此,诗人有足够的自觉。她说:“我一直以为写作的能力其实就是爱的能力,一个人爱的能力有多大,她所写出的文字就会有多少光芒,在具备了基本的文字技巧之后,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精神境界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唯有坚持,唯有歌唱,并承担起爱的职责”(《池凌云诗选·后记》)。
苦难考验了诗人爱的能力,坚定了她对爱的信仰。为了父母包办的婚约,池凌云于少年时就已遍尝远远超过一个少女承受限度的苦辛。但对于曾经给她带来苦痛和伤害的亲人,她在成年以后却报以更深厚的亲情。她为父母、为姐姐、为儿子,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当代诗人曾经为亲人写下这么多真挚的诗篇。比起对广大底层的关切,亲情当然只是一种朴素的感情,在一些人看来大概算不上如何伟大。但我关心的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感情,为什么在当代诗歌中却绝少深挚的表现?难以想象,一个缺乏亲情的人,会对底层民众有真正深刻的同情。我以为,越是朴素的感情,越是考验爱的能力的试金石。先要爱近处的人,对远处的爱才有依托;只有先爱具体的人,才谈得上爱人类。抽象地谈论爱人类是容易的,但是关爱身边的人却更有意义。正是她为亲人写下的这些真挚的诗篇,使我相信,当诗人说“只有真理和爱才能得胜”(《圣雄甘地》),“可以有爱。这是一种无穷的精神/支持你在人世轮回循环”(《偶然之城·一个婴儿被引诱出生的巷》)的时候,绝不是矫饰的表态和修辞,而是真诚的而且被始终如一的实行着的信念。
从这种“近处的爱”出发,诗人的爱走向了更多的受苦的人。在池凌云的诗中,无论是“抱住鞋,睡在各自台阶上”(《旧城·第五巷》)的孤儿,“拖着一条死亡的腿”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旧城·大沙堤巷》),被迫“坦白性爱的秘密”、“无法羞愧。无法做一个失踪的人”的底层妇女,还是无处可去而渴望“让我去死吧”的老乞丐(《过去的一天》),都从沉默的高墙后走出来,言说他们自己。底层写作、草根写作现今是一个时髦。但是以这类口号相号召的写作,我所见的大部分作品只是一种表态文学。诗人对于底层民众本身并无深切同情,对其生存的黑暗并无体察,更甭说此进入存在之黑暗的中心了。因此,这类写作大多只停留在时事报道的水平,自然也无法赋予民众的苦难以诗意的尊严。池凌云为受苦的人所写的诗篇却是建立在对民众的饥饿与黑暗真实而深刻的体察上,无一例外地联系着具体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诗人自觉到自己属于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爱憎相通、相连:“然而/我不应该为得不到慰藉而流泪/当我知道了那些苦难的人/我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四分之三泪水》)《大沙堤巷》中这样写到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把那条死亡的腿,藏到/宽大的裤管里,在冬天的夜晚/从里面开始结冰”。“从里面开始结冰”——这是真正和描写的对象合为一体,从自己内部把他人的苦难承担起来。这一承担和表态文学中泛滥的同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和阿伦特所说的“友爱”血脉相通——它要求、它呼吁着一种有意义的行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行动。也就是说,它不是媒体所热衷的那种公共的、短暂的同情——关于这点我们在汶川地震诗里已经长了见识,而是基于私人的、以生命为长度的“联合”。这是苦难和苦难之间的握手,姐妹和姐妹、兄弟和兄弟之间的握手——当两个苦难被我和你同时面对的时候,苦难就转化为救赎,沉默就转化为对话,恨也就转化为爱。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在谈论诗人的才华时,都强调想象力、感受性、语言天分的作用。但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感情或者说爱的能力才是诗人最重要的才华,想象力、感受性、语言天分没有爱的引导,对创作而言,只是一种消极的能力,单凭这些条件并不能产生积极的创作成果。就此而言,池凌云恰是我所看重的卓有才华的诗人。她所拥有的爱的意志和能力,使我对她的未来怀有更高的期待。
尤其令人感怀的是,诗人不但没有被苦难所屈服,反而把苦难转变成了命运赐予的特殊礼物,从中培养起对于生命、对于幸福的信念。她认为正是在苦难和贫乏中,“深藏着难以言说的幸福”①。她说:“生命中只有承受,没有仇恨”(《阔叶林与针叶林》)。拥有这样的信念,她不但“没有因失败而将自己抹去”,而且从苦难和失败中提炼出生命的最高智慧(《编织品》)。尽管诗人在她已经过去的四十多年生活中备尝艰辛,她依然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是个幸运的人”(《一个人的对话》),“平淡的生活依然泡沫四溢”(《在瑶溪,想起一位友人》),“但是的确如此,最普通的日子/水中流出了酒”(《旧城·水中流出酒》)。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在池凌云的诗歌中确实回响着一种幸福的旋律。白天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当夜晚来临,她一边流泪,一边却对自己说:“在小城里耐心过完一生是幸福的/等待一个不认识的人是美好的”(《昨天》),“需要一小块地毯/提醒我得到的一直很少/但却非常珍贵”(《偶然之城·小地毯巷》),“我希求你让我重新/幸福:拥有健康的父母,/即使劳作一生,依然失败/忍受四季的炎热和寒冷/清粥小菜,节俭度日/这一切多么好……”(《病中的父亲》)。这是一种力量,我不知道是诗赋予了诗人这样的力量,还是诗人把自己的力量给予了诗。《蜡像馆》、《雕像》、《白水冲遗址》、《少女喷泉》等诗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热爱。这些诗的主题与舒婷的《神女峰》有相通之处。舒婷说:“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池凌云则说:“生命之丰盈,只是一个任性的要求/假如有人从潮湿的石头上默默站起/她愿意跟随,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小屋”。但池凌云的诗刻画入微,多用客观的描摹,一改舒婷的意象性写法。《白水冲遗址》则展现了精妙的想象的和智性的精确配合:“多年以后,我看到另一些时光/洞穴中的炼丹术因埋藏太久而腐朽/而火不愿沉默,树走出篱外/惊愕的崖壁刮起狂风//这情景给我们带来新的空气和水/树向四周递送简朴的声音/我们在头上捕捉幻影之手/目睹一个人的面容走失/静谧,如一口古老的泉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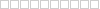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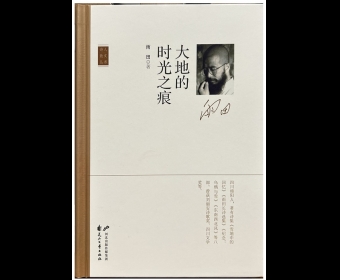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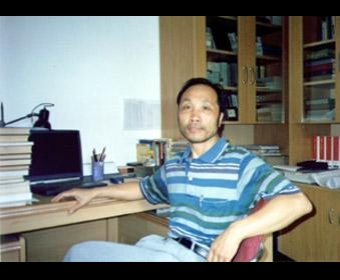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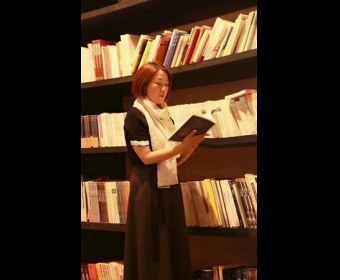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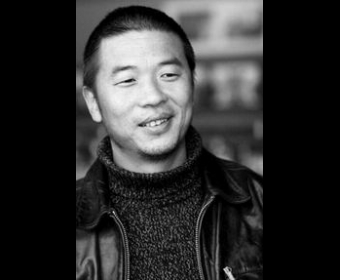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