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焱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熊盛荣,这是他发表作品和成名成家时用的。不过,身份证上写的却是熊焱,由于“熊焱”太像笔名,熊盛荣太像原名,没有办法,为了领稿费,写作的时候只好改成了熊焱,从而达到社会身份与作家身份的有效统一。熊焱老家是贵州瓮安,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他开始并不喜欢成都,觉得太慢,太慵懒,慢慢就发现,成都人善于在闹中取静、忙中偷闲,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他的生活哲学。作为《青年作家》《草堂》的主编,他对自己如何走上编辑生涯,总结为“充满了闪电般的奇迹”。《青年作家》十分重视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尤其是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起打造的青年文学奖项,如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成为青年作家们通往文学大师的一个前站。熊焱最看重年轻人的,是那股子朝前冲的气息,“对年轻的作家来讲,生涩一点没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哪怕在外已成家立业,不可能再重返故乡生活,在情感上故乡仍然是最后的依靠。
青年报:熊焱是你的笔名吧?你的原名叫什么呢?你能讲一讲和这两个名字有关的故事吗?你觉得名字,尤其是笔名,对一个作家和诗人有什么影响?
熊焱:我最早叫熊盛荣,在高中的时候改成了熊焱,先后是我的身份证名字。但由于我在高中时代就以熊盛荣这个名字发表了不少作品,所以从大学到大学毕业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我仍然用熊盛荣这个名字发表作品。但后来弃用该名,是因为收稿费很麻烦。那时稿费不打银行卡,都是寄汇款单。很多时候,我明明在稿子上写清楚熊焱是身份证名,但杂志社却觉得是我搞错了,非要写成熊盛荣。那确实也是,当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时,熊焱更像笔名。一个惊艳的笔名,某种程度上更能引人注目。那些太过普通的名字,确实容易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人名里。至少我都记得一些有趣的笔名,但他们的作品却几乎都记不住了。所以,写作者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青年报:据了解,你是贵州省瓮安县人,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好吗?
熊焱:瓮安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整个州少数民族很多,但我们县恰恰是汉族人居多。这片土地山水如画,是夏日避暑胜地。当年红军长征时经过瓮安,在一个叫猴场镇的地方召开了猴场会议,该会议明确红军强渡乌江、直取遵义的战略方针,被誉为遵义会议的前夜。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成功为红军赢得宝贵的休整时间。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有三处,其中一处叫江界河,立有战斗遗址的纪念碑,我读初中的时候常去那里玩。那时候还没有修建大桥,是轮渡把来往的车辆摆渡过河。后来因为下游修建水电站,渡口的战斗遗址已经被水淹没。
青年报:你第一次离开故乡和最近一次回故乡,分别是什么时候?在那片土地上还有哪些令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熊焱:2000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最近一次回乡是今年的春节,本来有几次想回去,又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而放弃了。目前最放不下就是父母还在故乡,他们已年过古稀了。但他们一直都不愿意进城,再则乡下空气好,食品健康,也挺适合养老。只是,故乡越来越空心化了,除了老弱病残幼还留守在那里,年轻人全都外出了,并且在城市安家落户,最不济也是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常常悲哀地假设,有一天那些年迈的乡亲全都去世了,故乡会不会成为一个寂无一人的空巢?我们为什么常常哀叹于故乡的凋敝、村庄的空寂,除了血脉深处那份浓烈的乡愁之外,更因为我们内心里存放着那份无根的漂泊感,哪怕你在外已成家立业,你也知道不可能再重返故乡生活,可是在情感上故乡仍然是你最后的依靠。
青年报:你是因为读了四川大学,才定居成都的。成都和瓮安,生活习性和人文环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你有没有一种漂的感觉?
熊焱:在最初,我并不喜欢成都,那时候的成都比现在慢多了,我觉得太慵懒,不过我慢慢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比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还长,可以说成都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虽然在这种洪流般的匆忙和喧嚣中,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无力的漂浮感,但成都终究是慢的,这种慢是一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态度,是成都人善于在闹中取静、忙中偷闲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我的生活哲学。每一次从外省回来,不论是由高铁到站,还是经飞机入港,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青年报:你的文学理想和审美是哪里培养起来的(或者说哪个影响更大一些)?你认为这两个地方哪个才是你文学的故乡?
熊焱:我个人文学的理想和审美都是在不断的阅读和写作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相对成熟的写作者,会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经验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美学判断,最好能形成一种体系,并且这种体系是在不断丰富、不断扩展、不断完善的。非要说哪一个对我影响更大的话,我认为是文学理想,只有心怀远大的文学理想和抱负,才会孜孜以求于美学上的丰富性和广阔性。文学理想是你持续不断地付出一生热情的助推剂,但落在写作实践上的更多是来自于美学层面的技术活,这两者都很重要,共同构成文学的故乡。

2 成为好编辑或好作家都很难,都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青年报:我们接着先说说你的第一个身份,你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你还记得发表的第一首诗和最近发表的一首诗吗?回过头来看看,你怎么评价这两个时期的作品?
熊焱: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98年第9期的《中学生读写》上,写的是我父亲劳作的场景。最近发表的诗是以组诗的形式出现的,这组诗大多是以中年、孤独、爱、时间、生命为主题。不论是哪一首,与当年的第一首诗相比,其实都有精神上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时间与爱。当然,当年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除了情感是真诚的,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这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人生、命运和生活的感知、体验是不一样的,对世界的认识和洞察也是不一样的。2017年我写过一首诗《岁月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二十岁时,我意气风发地豪饮最烈的酒/三十岁时,我穷困潦倒地咽下粗粝的风/眼看就要四旬了,我一次次的赶路仍然还像蹒跚学步的孩子//有时渴望深夜里闷雷滚动,把我从梦中喊醒/有时渴望昨日重现,我赶在日出前扶正倾斜的黎明/当我剥开掌心的茧子,第一缕晨曦就掀开了眼角的鱼尾纹”,这些都是时间变化的体现,尤其是心境不一样了。正如古人所言,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不就是在时间变化中的生命感知吗?所以,时间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年龄改变或者年份转换、季节更迭,而是生命内在和外在的变化。
青年报:谈到“时间的变化”,你的诗集《时间终于让我明白》,你能说说对于时间而言,你到底“明白”了什么?
熊焱:我所理解的时间,是一个立体、丰富、无尽无穷的概念。如果只把时间理解为年月日,理解为时辰、分秒,那就太片面了。我的理解中,时间包含了一切,人生的种种阶段是时间,沧海桑田是时间,日新月异是时间,万事万物的生长、变化,全都在时间里。因此,你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你对生命的体验和生活的认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时间中获得的。在时间中你似乎明白了许多,但同时在时间中你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因为无穷的困惑会随之而产生。比如《北风正在喊我回家》,不是简单的乡愁,而是对岁月流逝和生命渐衰的追问和无助,这首诗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就是雪:“几点雪粒落在我的鬓边,一年年地白啊/妈妈,这年岁真冷,正如我们头上的积雪/一直在逐渐加深,从不融化”,这里的雪是白发的比喻。《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了》沿用了雪的意象,同样是在表达时间与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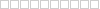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南方的南 评论 上海访谈|熊焱:读诗会让:把青年作家和草堂这两本重要刊物说清楚了,不简单
南方的南 评论 上海访谈|熊焱:读诗会让:把青年作家和草堂这两本重要刊物说清楚了,不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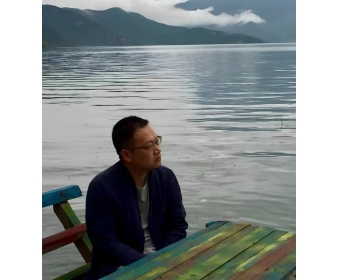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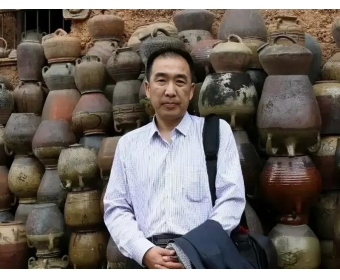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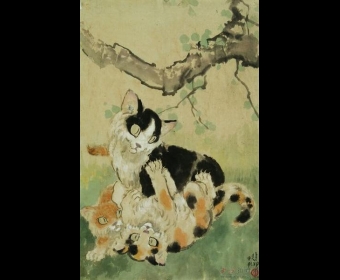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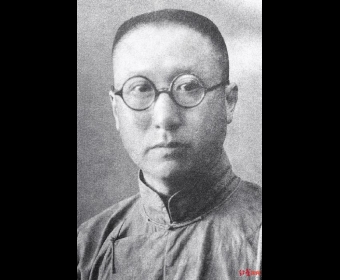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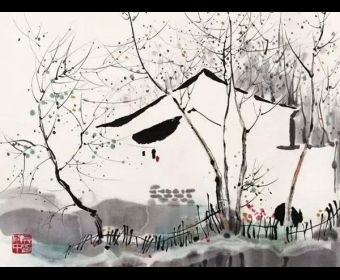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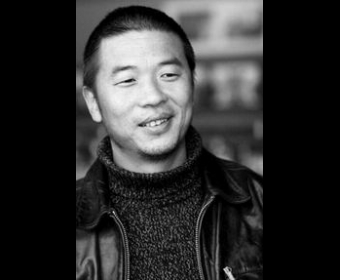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