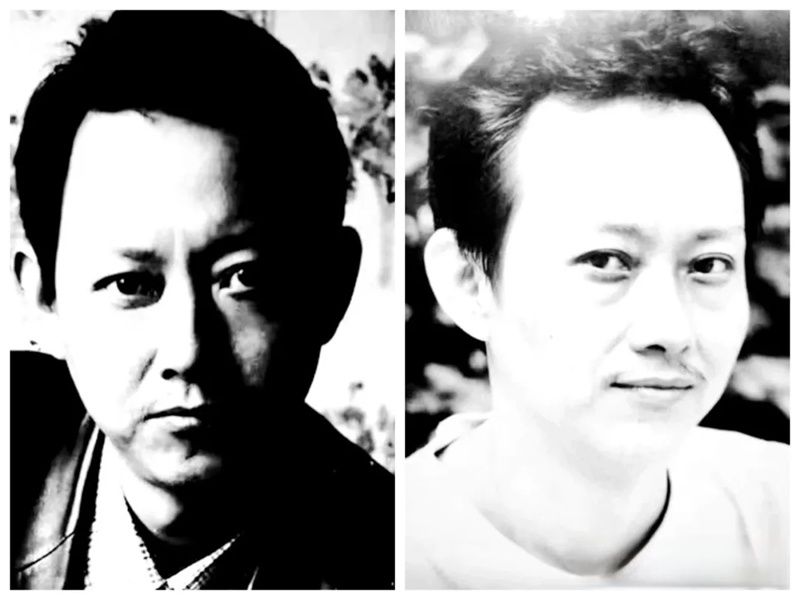
吉木狼格在1990年代
张后:不写作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写一篇日记如何,了解一下您的日常生活?
吉木狼格:今天本打算去参加一个画展,但老哥们莽汉诗人马松从北京回成都,约起斗地主,斗完喝酒。这是马松每次回来必走的流程,同其他相比,陪难得回来的老哥们玩最重要,幸好之前我没有表态要去参加画展。马松这次逗留三天,正在写的小说只有等他走后再写。
张后:您为什么写诗?
吉木狼格:18岁那年,我和许多青年一样,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认为人一生应该有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我该干什么呢?一天我突然想到写作,并尝试写起诗来。可以说我当初写诗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为了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诗的认知和态度已发生改变,现在写诗不再为了名利,以写出我想写出的诗为满足,写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抽烟、喝酒,戒不掉。
2025年5月21日成都

吉木狼格的诗
|西昌的月亮
如果我说西昌的月亮
像一个荡妇
正人君子会骂我流氓
如果我说西昌的月亮
像一个流氓
人们会笑我胡说
皓月当空的时候
我坐在月光下
看一本书
连标点符号都清晰可见
西昌的月亮什么也不像
它只是很大
|毕摩来了
感到了不详
去请毕摩
并把东西准备好
神枝、神草
当然还有一只羊
毕摩坐在法位
一边照规矩扎草
一边和蔼地闲聊
他的跟前放着一碗白酒
羊被牵羊的人牵着
神色安详而老练
好像彝人喂得羊
生来就有这个义务
其实人和羊不同
人一生要经历很多次
这种场面
而羊只有一次
随之将被宰杀
羊头和皮给毕摩带走
肉由大家分食
傍晚毕摩收起笑容
开始诵经
他反复举起铃铛摇晃
清脆的铃声伴着念词
于深夜传向屋外
也传进人们的心里
毕摩来了
妖魔鬼怪将被降服
人畜昌旺家庭和睦
有名的毕摩都很忙
在其他村寨
同样的声音
敲打着宁静的夜晚
哪怕外来文化
像傍晚的牛羊
纷纷进入山寨
|怀疑骆驼
已经是小心翼翼的时刻
门任然虚掩着
外面偶尔有声音
我开始想着骆驼
它在哪里呢,动作缓慢地
独来独往
那些声音在这时出现
我想是有原因的
不妨听一听
否则还不如寻骆驼去
看看他愚笨的样子,让它丢脸
门这样虚掩着
我疑心会被推开
跨进来一只非骆驼的前蹄
如此,今晚就那个了
我应该关紧门还是由他这样
其实既然这样了
为什么就一定会那样呢
关键是现在,除了骆驼
只有哦
只有一些风
从门缝吹进来
他们似乎并不针对什么
我的下肢被吹得凉飕飕的
很可能感冒
还是寻骆驼去吧
它愚笨的样子让人愉快
它显然知道
风
就像雨
自己把自己淋湿
我小心翼翼地望着门
悄悄酝酿豪气
到骆驼那里
一路上只要有声音护送
但不能高声喧哗
别走有瀑布的地方
骆驼一生孤独
声音太大会毁了它
它动作缓慢,活动范围却很广
要找到它不容易
声音可以少一些
水得备足
有一处它曾经停留过
现在住上了人
到时候不妨去问问
骆驼,并不是非找到不可
随便逛逛或者扯个谎就行了
但要当心,那地方
一个人的人品在于话多话少
比如在酒店里喝酒的人
劝酒的人
有关骆驼的事最好少问
那里旅店很小
异乡味很浓,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女人都性格外向
但某些部位
始终是藏而不露
既然为骆驼而来
非骆驼的问题只好放弃
骆驼曾经在沙滩上
不管从水里来
还是陆地,它
早已离开
只留下一些非骆驼的痕迹
让人猜想
我开始怀疑
是它引诱我还是我需要它
它不留下一点痕迹
但一直远远的,在笑
骆驼,该出现了,骆驼
究竟是什么颜色
有什么预谋
我当然明白
正如翻过这座山
就没有山了
声音也到此为止
到此骆驼和非骆驼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水
这一去
是否活着回来
就指望雨
但雨季已经过去
谁都免不了
在平缓入睡的沙漠
干干地躺下
| 当我在文化的时刻
不在文化的时刻
我在哪里
这一问,竟然无以回答
我在自己里,这算什么
灵魂出窍,是从头顶上升
还是从脚底下降
面对眼前的事物
城市,少女和路
视而不见又算什么
我在最负责和最不负责的时候
都要指责文化
而且心情比较激动
冷静后并不觉得崇高
也不认为低调
与文化对立
我出现在镜子中
砸碎镜子,我跟着成为碎片
是不可能的
决定了指责文化
那么文化像阳光我就指责阳光
阳光照着我
我就指责自己
如果对自己手下留情
对其他也网开一面吧
你看,这世界值得反对的
已经不多
|阿根廷蚂蚁
它们爬上船挺进欧洲
登陆后
以家族的名义迅速壮大
它们不断进攻
逐一消灭欧洲的蚂蚁
从而占领欧洲
它们继续乘船挺进别的地方
比如澳大利亚
不管在哪里
它们都能识别亲缘关系
并联合起来发动进攻
你可以轻易地捏死一只
阿根廷蚂蚁
但你无法将它们全部捏死
它们在洞穴生活
还是在野外作战
你得承认
世界不光是我们的
也是阿根廷蚂蚁的
来自公号《访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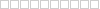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在水一方 评论 第三代诗人专访:西昌的月:受益了
在水一方 评论 第三代诗人专访:西昌的月:受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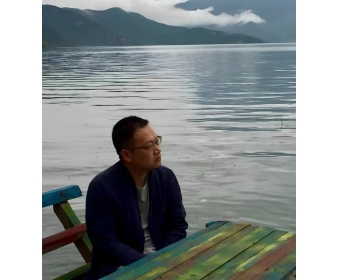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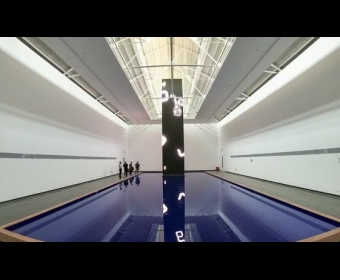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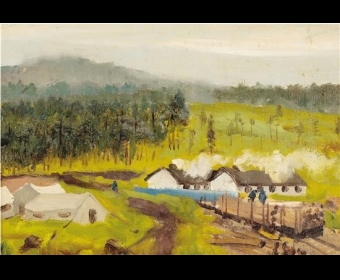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