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邻人与乡愁:荷尔德林式的凝神
乡愁诗学、梦想诗学和幽暗诗学,在我看来应是余笑忠诗歌创作中的三个重要方向,但他独特的抒情方式、诗歌技法与诗思深度又与当下众多重要汉语诗人的风格,格格不入。同样处于同时代的写作,为什么余笑忠会出现诗学立场的自觉性精神分野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在我看来余笑忠属于那种较为纯粹的诗人,除了阅读与写作,以及专业朗诵与音乐主持,他基本上不再从事其他的文艺爱好,一门心思地专注于诗歌的技艺与美德的积习。1799年1月,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给母亲的信中,称写诗为“人的一切活动中最为纯真”的行为。阅读余笑忠的诗作,即给人一种最为纯真的源自诗意的精神愉悦体验,哪怕是在阅读过程中会随着诗人的情感波动而产生幽愤和忧伤,产生悲悯与叹息,但是阅读的终极体验依然是愉悦的,甚至会带给我们形而上的诗意高度与哲学思辨。余笑忠的诗歌意象集成几乎是没有杂质与杂念的,他迥异于一些诗人喜欢在诗歌中大量堆砌诗歌意象,故作高深与玄奥;余笑忠不会,他总是尽力剔除诗意中的杂质,让他的读者在一种朴实、真诚的阅读体验中抵达他的诗学境界,却不失汉语诗学的深度与难度,这正是余笑忠诗歌最令人称道之处。正如诗人自己所言:“有所思的诗,不如若有所思的诗,无名的天真状态的诗”。而我更加看重和敬佩的是余笑忠在诗歌中所袒露的“思想者”角色,这也是大多数他的读者所忽略或没有完全意识到诗人余笑忠值得观察的精神性面孔。余笑忠是一位有着悲悯情怀的诗人,近二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与历史与现实事件有关的诗歌作品,包括近期的世界疫情灾难期间,这些诗歌作品是构筑和支撑一个大诗人成为可能的必要的诗学正义与伦理的基础,这样的重要诗作有《一九七六年》《公元70年》《中国病人》《他们这样屠杀一头耕牛》《南京,1937》《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悼巴金》《书事》《2010年春,云南的愁容》《哭墙》《Primo Levi》《Covid-19肆虐时》《有人》等,这些诗是疼痛之诗,哀悼之诗,悲悯之诗,诗人用自己独特的感受记录了这魔幻人间的善与恶,丑与美,诗人心中既有大悲喜,亦有万古愁,而余笑忠写于2017年的《哀邻人》则让我更加清晰地窥见到,这是一位思想深刻的诗人,一位拥有救赎意识的诗人:
世上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我老家的邻居所遭遇的
村中一位妇人过世
他生平头一遭去抬丧
有人怪他一路上摇摇晃晃
第二天他口眼歪斜,疑似中风
到县医院就诊后有好转,能自理
后又复发,不能言语
送省城求医,不治而亡
旬日之内,他也被人抬上了山
时年六十六岁
那人算不上一个好邻居
去年为宅基事还想对我叔叔大打出手
但他遭遇了世界上最悲哀的事
纵有不良之举也当略去不提
那些为他抬丧的人
都如壮士,都是良善之人
——《哀邻人》(2017)
谁是我们的“邻人”(prossimo)?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公元354 - 公元430)的回答是:“每个人”。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 )则认为,在主体之中非主体的东西,就是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邻人” (neighbor)概念中的非人,是主体中的他者、他性。思想家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1929年的博士论文中即以“邻人之爱何以可能”为主题,围绕奥古斯丁的爱的定义展开诠释和质疑。阿伦特指出,在爱的秩序中,奥古斯丁区分了“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近旁”和“在我们之下”的三层爱的等级。“在我们近旁”之物——我们自己、邻人和身体,作为跟我们自身直接相关的关系项,在此三重等级中处于中间位置,与“我”并列。阿伦特认为,这一共同起源造成了人类的亲属关系和共同命运,在此意义上是一个“命运共通体”(Common destiny)。从而,应当爱你的邻人的第一个理由是:邻人跟自己在罪和死亡上的平等。邻人的不幸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随时警醒我们自己跟邻人有同样罪恶的过去,同样最终面临死亡的悲惨命运,因而都需要救赎。[16]阿甘本在2020疫情期间多次发声,他认为中国疫情是一种“例外状态”,并且意识到疫情灾难中“人际关系的恶化”:“一个‘他人’,不论是谁,不论是不是亲近的人,都不可以靠近、也不可以接触。……‘邻人’不复存在。”(阿甘本:《论感染》)
余笑忠的《哀邻人》写于2017年,然而,我们经历了2020年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灾难之后,我们更加意识到这首诗杰出的现实意义。一个成熟睿智的诗人总是善于在一切卑微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真知,这种发现极是一种高超的诗思创造行为,余笑忠极为擅长在卑微事物中发现哲学思想的诗思行为。此次疫情期间,余笑忠同样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继续深刻的灾难叙事与人性反思。夏可君在一篇诗评中如此评价余笑忠的灾难叙事与日常记事:“余笑忠几乎是我读到过的中国诗人中,最为关切日常生活及其灾难的记事者之一,诗作中的一切看起来如此日常。但一切看起来却又如此不同,其目光穿透了人世与历史的沧桑,穿越了动物与梦境的沉默世界”,“诗性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迫使词语进入例外状态,进入残剩状态,进入混杂状态,直到所有的时空都被击碎,从而让诗具有一种识别的能力”[17],甚至夏可君称余笑忠为“灾难边缘最为深切的旁观者”。从“爱邻人”到“哀邻人”,我们的时代叙事已发生巨大蜕变,现实社会已让人们逐渐丧失“爱邻人如爱己”的土壤和空气,而更多的社会性事件,却让诗人不断地哀悼我们的“邻人”,从而导致同时代诗人的哀悼意识与诗学正义不断滋生。诗人对人性——善与恶——的深度思考一直贯穿于他几十年创作历程之中,早在十年前即写出《良人歌》,十年后写《哀邻人》,随后又写出了《废物论》,足以清晰洞察余笑忠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思考的渐进过程:
我弯腰查看一大片艾蒿
从离屋舍之近来看,应该是
某人种植的,而非野生
药用价值使它走俏
艾蒿的味道是苦的,鸡鸭不会啄它
牛羊不会啃它
站起身来,眼前是竹林和杂树
一棵高大的樟树已经死了
在万木争荣的春天,它的死
倍加醒目
在一簇簇伏地而生的艾蒿旁
它的死
似乎带着庄子的苦笑
但即便它死了,也没有人把它砍倒
仿佛正是这醒目的死,这入定
这废物,获得了审视的目光
——《废物论》(2017)
“废物”在诗人的隐喻中,不是剩余之物,也不是无用之物,它包藏着世间万物,包藏巨大的黑暗,以及生命中无限的灵韵与微光。2018年春节,我在诗人的家乡白茆村余油铺见到了那棵高大的香樟树,依旧矗立在万木争荣之中。诗人在诗中抒写的“醒目之死”,再次应证我的判断与洞察——余笑忠诗歌中潜藏的寓言告知意识与暗黑诗学的启迪精神。而诗人书写的“醒目之死”——“活着的死”,已经触及到众生的灵魂与肉身,鲜活与阵亡,衰败与腐朽,醒目与暗淡,高大与卑微,包括我们繁衍千年的汉语肉身,诗与词的肉身,历史与政治的肉身,语言和人类一样面临共同的命运:衰老与死亡。余笑忠的诗学构筑土壤,主要来自递进式的乡村经验与时代叙事,而他处理乡村经验的能力于我之观察,在当代诗人中是特别突出的。他擅长把朴素的、困苦的、日常的乡村经验,以及幼年记忆,上升到哲学层面和精神层面,甚至他能把“人与事”中最为细微的言行转化为神奇的诗意表达,并让这种诗意呈现出它应有的“幽暗”、“光亮”与“震颤(本雅明语)”,我珍惜这些幽暗、光泽与震颤,并视为一种“神性”,它们呈现出诗人内心深处一种宗教般的“汉语乡愁”。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Harold Bloom,1930-2019)说:“一个诗人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
这一刻我想起我的母亲,我想起年轻的她
把我放进摇篮里
那是劳作的间隙
她轻轻摇晃我,她一遍遍哼着我的奶名
我看到
我的母亲对着那些兴冲冲喊她出去的人
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凝神》(2009)
《凝神》是余笑忠现已出版的诗集中我最喜欢的诗,没有之二。这是一首杰出之诗,永恒之诗,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诵传这首诗,尤其是诗歌的最后一节彻底击中了我,让我心醉神迷,一下也回到了自己的幼年,回到了姆妈的摇篮里:“我看到 / 我的母亲对着那些兴冲冲喊她出去的人 / 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这一刻”,即是时间叙事中的“神性”存在与定格,甚至我能从诗句中读出诗人记忆深处隐秘的“圣母意识”与舔犊之情。余笑忠的《凝神》让我想起梵高的油画《摇篮曲》(1889),梵高此画灵感来自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笔下的纺纱工人,画面上的母亲则是当地邮差鲁林妻子的形象。梵高没有直接画出摇篮中的孩子马赛莱,而是用摇篮上的绳子暗示婴儿之存在。温柔而坚定的妻子手中的绳子,仿佛是母子之间神秘的纽带。《凝神》仿佛一首首扣人心弦的摇篮曲,特别适合在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摇篮曲》的音乐中朗诵这首诗,诗歌中伟大的母爱完全可以与那美妙动人的摇篮曲融为一体,在我们耳际回荡。“凝神”是一种专注,爱的专注,情感的专注。母亲在劳作的间隙,一边摇着摇篮,一遍遍地喊着诗人的小名,门外有人来喊母亲出去,她却不愿意离开摇篮中的孩子,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凝神》的温暖与爱意让我不禁想起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1861—1941)摇篮曲般的诗句:“你无穷的赐予只注入我小小的手。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还有空处可供充满。”[19]诗人所有的乡愁意识全部来自他生命与记忆的摇篮,包括诗人的乡恋与乡愁,“词语的肉身”(雅克·朗西埃语)。余笑忠在他的短诗《目击道存》(2015)中有如此精妙的抒写:“阳台的铁栏杆上有一坨鸟粪/ 我没有动手将它清理掉,出于/ 对飞翔的生灵的敬意/ 我甚至愿意/ 把它看成/ 铁锈上的一朵花”。余笑忠最为擅长抓住叙事的细节,他有意识地在诗歌中凸现叙事细节的重要性,从而来突出诗性的引爆点,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精神震颤与思想共鸣。在诗歌写作中,可以把“叙事的细节”理解为“语词的细节”,而这个细节与诗人的身心紧密相连,我手写我心,我思故我在,因而我们又可以理解为“词语的肉身”。阅读余笑忠的诗歌,往往让读者全身心地沉浸其间,时常体验到来自语词内部的幽暗的肉身之感,这种罕见而新颖的语言修辞表达,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处,给读者重重的一击,而让诗意四溅:“梨花带雨,春衫沉重/ 我死之后旧情有望复萌/ 但不能是这一河黑水、一地黑沙/ 鸡犬叫嚷:要回就回小国家”(摘自《清明日大雨》,2009);“在我们之中,必有一个高龄孕妇/在她的神面前/ 她为日益艰难的躬身/ 而羞愧”(摘自《羞愧之诗》,2012);“难以置信,杀了那么多的鱼/ 为什么没有一条/ 发出哀鸣”(摘自《哑口无言》,2001),等等。一首《弱肉》更是把余笑忠独特的肉身意识与诗性正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候在病中,我们虚弱得足够进天堂。”[20]
那天堂是白色的。
波涛万顷,数万黑奴共系于锁链
数万只蚂蚁,热锅更热
沐浴者
有时长久仰面如接滂沱大雨,以期悲苦
彻底委地
以期待老树著花
有时候在病中,我们指指点点,凭一支粉笔
凭满口达尔文主义的白牙
我摔得鼻青脸肿的那一日:山中玉石,苍苔裹身
——《弱肉》(2008
美国作家海明威(Hemingway,1899-1961)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它继续存在着,永远拥有生命力。每重读一遍,你看得到或学得到新的东西”。《凝神》正是这样的一首有着神秘意境的杰作。余笑忠的诗歌风格是多变的,像一个性格演员,但是他所秉持的诗歌立场或曰诗歌要义,却是单纯的、本色的。像《凝神》《雾中》《原因》《清溪》《目击道存》《假死之树》《满月之夜》《白鹤高鸣》《礼物》《清明日大雨》《正月初六,春光明媚,独坐偶成》等一批短诗,极具汉语中古诗学气韵,并且带有古典、温柔、敦厚的人文气息,深刻地表达了诗人超验而空灵的人生体验与诗性哲学。余笑忠的诗歌杰作太多,另一首杰作《红月亮》,有效佐证了朗西埃“词语肉身”的诗学理念,包括诗人精神记忆中的饥饿意识与死亡意识,以及他对诗歌美学探求的执着与深刻:
想起和父亲在大河里看见红月亮的那个傍晚
那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我们的腹中
空空如也。红月亮
升起在东边的山头上
为什么它变成了红色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和父亲望着月亮
不同于父亲和我
不同于流经我们的河水
在少年的我看来,孤悬的月亮是没有源头的
那一轮红月亮
那一刻,全世界的河川都归它
但只有流经我们身边的河水
在不一样的月光下,泛起小小的波澜
——《红月亮》(2014)
“红月亮”又称“血月”,月全食之时,会出现血月之相,因而各地均有关于红月亮的神秘叙事方式,以及暗黑的、魔幻的传说。余笑忠的父亲因意外逝世于2013年10月,《红月亮》为父亲而写,诗人回忆与描述少年时代与父亲一起见到的红月亮。此诗看似怀念父亲的诗,但是诗人也是在借助怀念父亲,而回忆一个过去的时代。此诗本质上依附着另一种时代叙事的幽暗与宿命,它们关涉饥饿、苦难与死亡的肉身记忆,它们依然是诗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时代乡愁的诗思,诗人依然是永恒记忆中“河边少年”,“报信少年”,一直惯于抒写他内心沉重而神秘的“天真之歌”(布莱克语)。我发现余笑忠有诸多诗作标题,诗歌的画面感、立体感很强,这些诗作同诗人观阅过的影像和一些书籍有着或明或暗的意象关联,比如:《愤怒的葡萄》《梦游者》《黑钢琴》《南京,1937》《中国病人》《神秘地宫》《哭墙》等;尤其是音乐,比如《谐谑曲》《思乡曲》《小交响曲:春天》《哀歌》《春之歌》等。这种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借鉴、相互生发的写作意识,值得提倡,我个人也经常从艺术作品中寻求灵感。这种诗人的个体精神创作行为,值得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诗歌与电影、与音乐的关系。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 )一直坚持在他的“电影史”中用“爱”和“诗”来对抗逻辑,对抗纯粹理性,因而他的电影中普遍存在着一个对应的物质载体。同样,在诗人的诗歌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电影影像介质的精神载体。诗和音乐(包括歌)是“古老的艺术”,而电影不是,电影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产物,因而电影需要诗和音乐来充实它的存在价值。相反,伟大的诗歌总会拒绝纯粹理性,当我们在现代性的诗歌中逐渐遗忘了那些古老的修辞与信仰,遗失了那些古老的图腾和文明墓碑,我们需要现代性的工具来巩固与延展“古老艺术”的生命力,比如电影,比如音乐。匈牙利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2019)说,“美”内在于生活中,而“诗”即是“美”最伟大的呈现方式之一,而我们的诗人所表达的最为深刻的诗意存在于体验与想象之间。因而,电影式的叙事场景与抒情意象,包括音乐的各种节奏与节拍,是诗的另类呈现。诗人余笑忠作为一位资深的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爱好古典音乐,对音乐的深度理解,无疑影响到他对诗歌的节奏、内在韵律的认知与运用;而事实上当我阅读余笑忠的诗歌,会发现他十分注重把握和控制诗的韵律与节奏。古典诗意与现代诗意的杂糅,显然也是当代汉语诗境所呈现的另一种现代性,或者说,这是他写作中又一个隐秘的技艺,来自古典诗学的经验与记忆:
梨花带雨,春衫沉重
我死之后旧情有望复萌
但不能是这一河黑水、一地黑沙
鸡犬叫嚷:要回就回小国家
——摘自《清明日大雨》(2009)
余笑忠是一位赤诚的具有还乡意识的诗人,荷尔德林式的还乡者。他的“还乡意识”几乎遍及他所有的诗歌。本文所言的“还乡意识”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还乡”,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上的“还乡”。荷尔德林在给他的友人比伦多夫的信中写道:“越是研究家乡的大自然,它就越强有力地感动我,雷雨对于我们有些神圣,不仅在其最狂热的显现中,而且同样在作为力与形象的景象中,在天穹的其余形式中,光发挥着它的作用,构成了民族的准则和命运的方式,它急匆匆的到来和隐退,森林的特征,大自然的不同特点在一个地方汇集,地球上所有的上帝都环绕着一个地方,而现在环绕着我的窗户的哲学之光是我的欢乐;我是如何一路至此,愿我能留住它!”[21] 阅读俄罗斯诗人叶赛宁( Есенин,1895-1925)和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我们能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俄罗斯乡愁;阅读德国诗人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我们也能感受到浓烈的德意志乡愁,而他们的乡愁诗学却又大不同于同为德语诗人的荷尔德林,而生活在大陆的诗人余笑忠的乡愁诗学与他们之间又有着太大的迥异之处,甚至他极少在诗歌中直接说出“乡愁”二字,但是我们却不能否定他的诗歌与“乡愁诗学”的关联。
五、哀悼与悲悯:幽暗诗学的介入
1947年,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提出“文学介入”一说,同时也是第一次正式将这个哲学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在萨特看来,写作就是“介入”,但是他强调只有散文是介入的,诗歌、音乐、艺术是一种非介入的行为。当他这种论点遭到质疑与诘难时,他却反问别人:“我为什么也要让诗歌介入呢?”就在当年,萨特在《1947年作家的处境》一文中同法国现实联系起来,“介入”、“介入文学”的概念迅速从他的文章中消失,取而代之却是“处境”、“处境文学”等新的概念。这也足以说明,萨特的理论是善变的,随时有可能出现自我颠覆与自我纠偏。评论家王岳川教授(1955- )注意到萨特这一反常现象,王说:“不妨说,当萨特在‘介入’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时,他的立场在哲学家和政治家之间滑动,他通过概念的转换,在文学平台上已悄悄完成了从抽象哲学思考到具体政治关注的位移。”[22] 事实证明,萨特的不切实际的“文学介入论”落空了,全球化的诗歌、雕塑、音乐的艺术史,也是人类文明的“介入”史。1968年,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新知识分子”当然包括诗人与艺术家,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放弃过去“存在理论”的时代症候,间接承认了诗人与艺术家的“介入”力量。
诗歌的介入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富有现代性的诗学精神。记得有人说过,“介入”是文学的大法典,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大法典也就是介入的外延的形象指代,外延是十分宽广的,它包括先锋性的介入、日常经验的介入、社会现实的介入、自由独立精神的介入、人文传统的介入、历史观的介入、身体的介入、诗歌伦理的介入、艺术的介入、历史的个入、暴力美学的介入、环保主义的介入、社会思潮的介入、政治的介入等等,总之,介入的内涵主要是指诗人主体意识的植入与强指和能指,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修辞的;它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宗教的;它可以是乌托邦的,也可以是形而上的。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会意识到诗歌的“介入性”也会存在着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即便是敌意的介入,同样也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荒诞的——自觉的敌人,荒诞的敌人。作为一个诗歌读者,我支持和尊重诗人在诗中的种种介入行为。同样,作为一个批评者,我更加期待批评家的介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们普遍缺乏介入精神。唯有少数的批评家勇敢地介入了时代的荒诞性,介入了公众性生活,介入了历史与现场。
余笑忠的诗歌作品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即具有时代叙事、灾难叙事的“介入性”,而且他介入的思想与技艺,均是一流的,且具有时效性与先知性。而让我钦佩的是透过他的诗句,我们能深切地感受诗人各种情绪在理性与节制的练达中呈现于他的诗行之中:或愤怒、或幽怨、或叹息、或悲伤、或哀悼、或呼愁……,诗人把自己的幽暗诗学毫无保留地呈现于诗歌之中。余笑忠幽暗诗学的“介入性”表达,以及个体精神的确立、担当,正是我敬重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正是这种诗学正义的介入,丰富和成就了一个杰出的“同时代人”的思想者形象:
这人间有高处,但你们攀爬不上
你们的父亲母亲也攀爬不上
这人间有歌声,照样有歌声
但你们的嘴里含着污泥浊水
你们的父亲母亲嘴里也含着污泥浊水
这人间有几间脆弱的教室
经不起野蛮的洪流从背后一击
这人间有一条河吞下你们
然后又风平浪静
这人间有一个悲哀的日子
它吐不掉,永远吐不掉
它要被永远诅咒
孩子们,这人间有花
抛向你们的是落花
在流水之上,星光之下
它们围绕着一支烛台
如果我们誓言那烛火永不熄灭
是不是死亡的数目还将添加
——《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2005)
法国作家福楼拜(Flaubert,1821-1880)说,一个诗人应该把自己隐藏在作品里,如同上帝把自己隐藏在万物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又说,诗比历史还真实。诗人于坚说,诗是世界的隐喻。因而,“隐喻”总在一次次的诞生,就像黑暗中的“婴儿”。诗思的隐藏与外露,是两种不同的写作路径,目的也不一样,该藏就藏,该露就露,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里,“隐喻”成为一种必修的诗学课,并且隐喻成了幽暗诗学的匕首。于坚说,中国正处于伟大悲剧与喜剧交替出现的生动时期,使中国诗歌拥有巨大的心理的、历史的、当下的文化空间和悲天悯人的气度;但于坚所言的诗歌气度不是当下每一位诗人有能力持有的,而余笑忠已经像第三代中的杰出诗人一样,渐具独立清醒的诗学面貌和卓尔不凡的诗学气度。我们的时代呼唤更多有抒情能力与汉语气度的诗人,也呼唤更多的诗人在幽暗诗学的领域里进行更加激荡人心的创造与想象,写出更多杰出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甚至,我认为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极为匮乏并且亟需“哀悼意识”与“批判意识”的诗学治疗,而“哀悼意识”与“批判意识”是幽暗诗学的灵魂羽翼,一个肩负诗学正义使命的当代诗人自然不可失却幽暗诗学的理想。这个理想,需要一代代诗人的锻造,决不是某一个诗人、某个时期所能完成的。批判是一种力量,哀悼也是一种力量。美国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说:“如果哀悼要求我们明白所失之物究竟是什么,由于哀悼具有神秘未知的一面,由于失去某种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令人困惑,因此哀悼将一直持续下去”[23]。如果我们失却了批判的土壤和权利,那么,一切就从“哀悼”开始吧:
怎样的石头
怎样的高墙
教堂只余半壁,旋即
罗马人的怒火
将它化为齑粉
怎样的双手
抚摸石头
如抚摸一扇门
不复存在之门
因此抚摸的是
另一双手,手心贴着手心
抚摸的是另一个人
光洁的额头,蒙霜的睫毛
摸到了睫毛油,摸到了灰烬
摸到了永别之前
屈膝深埋的……
在昏花的老眼看来,黎明
即已沦为黄昏
“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
所有的高墙
都有痛哭的一面
你有不能揉掉的
眼底之沙。而哭墙
哭墙的石缝里
还会长出青草
——《哭墙》(2011)
在我看来,余笑忠诗歌的幽暗意识更好地呈现了诗人-思想者的哲学气质,这也是我十分看重和喜欢他的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他赢得众多诗人的敬重的重要原因,这种哲学气质却又不被普通读者所发现和熟知。余笑忠擅长将一些带有哲学阐发意味与隐喻意味的词汇或语句注入诗歌中,让它们成为诗歌中的最为耀眼的诗意聚焦点,并且将聚焦点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忽略不计的细小事物相关联,生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诗歌意象与思想火花,从而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震颤的心灵感应,产生诗思的共鸣;甚至他可以像一位沉稳的语言匠人,一位技术高超的解剖医生,对历史与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讽刺和追述,把最炽热的部位、最细小的血管、最敏感的经络呈现在他的读者眼前。这种源于灵魂深处的思考与长久练习,对细小事物及其命运的观察、解剖,以及重新构结“词”与“物”的关联,“人性”与“物质”的关系,余笑忠这些卓越的诗思,让自己成为“诗人思考人类与自然命运”的杰出旁观者,成为典范。因而,从哲学气质这个层面上来看,诗人余笑忠与哲学家夏可君之间近三十年的友谊与悻悻相惜,是好理解的。这也是夏可君进入诗学领域,评论最多的一位诗人为何是余笑忠,而不是他人。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和诗人,关于“语言”与“灵魂”之间的经典性观照:谢林(Schelling,1775-1854)与但丁(Dante,1265-1321),黑格尔(Hegel,1770-1831)、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与荷尔德林,德里达(Derrida,1930—2004)、阿甘本与策兰(Paul Celan,1920—1970),本雅明(Benjamin,1892—1940)与布莱希特,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与里尔克(Maria Rilke,1875-1926)……。虽然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荷马(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也未幸免。但是两千年后,西方哲学家却开始向诗人索求人类精神的奥义,无异于是在向诗求教。比如尼采(Nietzsche,1844-1900)式的诗人哲学家的出现,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转向诗的阐释,20世纪的现代性哲学应该倾听诗人的声音。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或者说哲学与诗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乃至争端。自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在西方哲学与诗学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思想潮流,成为人类意志自我纠偏的精神运动。而现代性诗人更应该敞开灵魂,主动地向诗性哲学靠近,向诗性正义靠近:
所有亮着的灯都在制造谎言
但你不会说谎,所有暗自
流下的泪水,不会
所有亮着的灯都是赤裸的
我要你亮着,赤裸着
我也必须赤裸着,赤裸着
我们如此孤独。在隐语和行话中
我们愈加孤独。比如沙漠中的海盗
比如失明者眼中
最后的微光
——《“深邃而普遍的黑暗”》(2011)
结语
余笑忠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并且他有一个保留诗歌手稿的好习惯。这个具有书家气质的勤奋习惯,居然坚持了二十余年,令人敬佩不已。再过五年,诗人余笑忠也将迈入花甲之年。从余笑忠目前每年五六十首的创作效率,可以想见诗人的创作生命力依然旺盛。美国诗人奥登在谈及“大诗人的标准”时,简单地概括为五个标准:“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余笑忠的诗具备这五个标准。奥登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奥登所言的“最后阶段”,即可以理解为诗人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对于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而言,“晚期”是一个超越自我与过去的时空概念;对于美国思想家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而言,“晚期”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充满记忆,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24]或者说,诗人的晚期风格,是诗人抵达终极理想的可能性存在。有迹象表明,余笑忠也在努力让自己的诗歌写作正在抵达阿多诺与萨义德所言的“晚期”境地。当然,“晚期”的到来,意味着诗歌叙事中的腐朽与神奇、黑暗与光明,也会接踵而至。“晚期”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年轻虚构的“老年的冯塔纳”,“晚期”又是所有大诗人葆守一生至暮年而对“天真”与“童年”的返照,而非“时代的落伍性”。当代批评家耿占春(1957- )论述亦精妙:“‘晚期’意味着一种‘遗嘱性’的写作”,亦适合于我对余笑忠晚期风格的理解,也是我对余笑忠最大的期待与敬畏;而余笑忠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之心,不禁又让我杜甫的诗句,亦可视作对所有身处异乡的诗人之告诫:“他乡悦迟暮,不敢废诗篇”。我们有理由相信,余笑忠将会在他的晚期风格中完成他的诗学理想,完成对当代汉语个体诗学的另一种锻造,为当代汉语新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20年6月27日,初稿于团城山。
注释:
[1] 参见《蕲州志》,[清]光绪时期,2009年重刊本,第40页。
[2] 参见《接梦话》,余笑忠 著,宁波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3] 参见《巴黎的忧郁》,[法]波德莱尔 著,郭宏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4] 参见“原乡书院”微信公众号,《诗宴:荷尔德林诗选 》,钱春绮(1921-2000)译,2018年3月6日。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oH8IWFMsYvatLBT520VCTw
[5] 参见亨利·米肖《信》,Pierre译。网址:https://www.douban.com/note/634503416/?type=like
[6] 参见《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尹星 译,陈永国 校,河南大学出版社。
[7] 参见《于坚诗歌评述》,作者 段凌宇,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论文第18页。
[8] 参见《词与物》,[法]福柯 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7月第1版,第37页。
[9] 参见《文学的政治》,[法]雅克·朗西埃 著,张新木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 页。
[10] 参见《我,眼睛,声音》,[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王立秋 等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11] 同上,第112-113页。
[12] 参见《姿势的诗学》,夏可君 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诗歌的调校:余笑忠的原音》,第266页。
[13] 参见《梦的释义》,[奥]弗洛伊德 著,张燕云 译,陈仲庚 沈德灿 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一章第7页。
[14] 据2019年6月29日“余笑忠诗集《接梦话》分享会”录音整理。
[15] 参见夏宏:《于波动中转折——余笑忠诗歌漫论》一文。
[16] 参见《邻人之爱何以可能:阿伦特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作者 王寅丽,《文化研究》杂志,2016年秋季卷。
[17] 参见《余笑忠的诗日志:来自“小国家”的伦理》,作者 夏可君,2018。
[18] 参见《疯狂的谱系: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到阿尔托》,米歇尔·福柯 等著,孔锐才 等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53页。
[19] 参见《吉檀迦利》,泰戈尔 著,萧兴政 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第2页。
[20] 余笑忠注:此句诗引自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特的诗《病》,方若冰 译。
[21] 参见《荷尔德林书信选》,[德]荷尔德林 著,张红艳 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223页。
[22] 参见《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作者 王岳川,《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3] 参见《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2版,第31页。
[24] 参见《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 著,阎嘉 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1版,第11-13页。

江雪(1970— ):当代诗人、批评家、艺术家。原名江山,出生于湖北蕲春,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1979年开始学习书法、绘画,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90年开始学习篆刻。1987年创办荷西诗社及《荷西诗刊》,1992年创办《解决》,2005年创办《后天》杂志,同年创立“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迄今举办八届。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国内诗歌节、艺术节及学术交流活动。著有诗集《汉族的果园》《江雪诗选》《牧羊者说》,评论集《后来者的命运》《抒情的监狱》《理想与棱镜》(即出),摄影集《饥饿艺术家》等。现供职于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黄石书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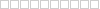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南方的南 评论 江雪:余笑忠论 | 风骨与:雄文
南方的南 评论 江雪:余笑忠论 | 风骨与: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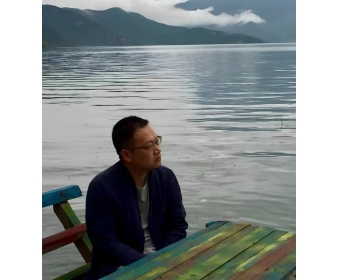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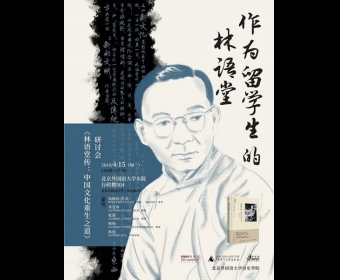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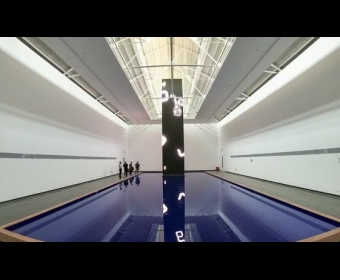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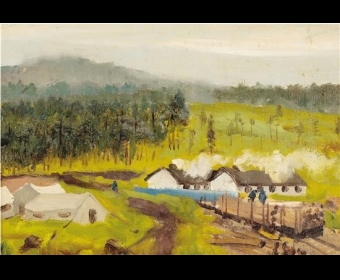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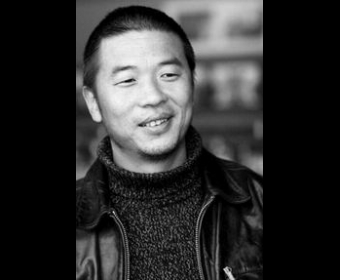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