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房子(右3)与来自西藏的诗人贺中(右2)喝酒
何房子,本名何志,男,1968年生于湖北,198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工学学士,199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文学硕士。新闻高级编辑。从事媒体工作20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诗歌写作,大学生诗派的参与者。《诗歌报10年精华》、《四川新时期诗选》、《第四代诗选》、《湖北当代诗人诗选》等重要选本有其诗歌痕迹。
古佛洞的一夜
古佛洞的尽头是低矮的棚屋屋顶偏西
迎向枝头的暮雪
要到明年才能换来黑夜
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
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
总是早早的吹灭蜡烛
用单薄的身子梦想着美好的生活
屋外的风在草丛中潜行
也潜移默化
沉睡的大多数 在我的身旁
在这雪落无声的一夜
一支恍惚的蜡烛开始说话
一夜的风雪不能叫做遭遇
一把陷入怀念的椅子
不能自拔
不能承担一个人的重量
斜坡上的村庄
村庄沿着斜坡缓慢移过来
有如冬天迅疾降临的夜晚
瓦是黑的。瓦在屋脊
留住了不动声色的时间
过年的孩子走出拱立门
他目光覆盖之地
仅仅只是一些沟渠和蔬菜
远方比一年一度的新衣
还要遥远
附近的一所小学人去楼空
黑板上简单的汉字被擦去
被斜坡上的村庄反复传唱
“小儿郎呀,背起书包上学堂”
老人们这么说。老人的身后
是一扇打满了补钉的窗户
里面闪烁了多年的油灯
有着游丝般细密的皱纹
而当高梁和大米散落于集市
孩子们东奔西走,大部分
学会了用大碗喝酒
到了该告别的黄昏
我才发现这泥土搭起的村庄
还包含着如此隐痛的一面
还来不及深入月亮就涌出了桂花和斧头
半山腰的树
我熟悉这样一棵树 在冬天
山顶的积雪开始掩埋石头
而它躬身于自己的阴影之中
从来没有移动过
起初还是一点伤痛的绿色
后来就成为了
这半山沉默的一部分
我经过时
正是一场大雪之后
寂静而白的山林露出
几根树枝 那其中的一根
把半山腰的树挽留在半空
犹豫 抑止
这晚年的梦境
把我的喧响遗忘在来时的路上
阴影 以及雪下的峭璧
划破黎明 一半被大雪照亮
另一半在一棵树的黑夜前回首
有谁看见了它秘密的成长
秃头张于
情种、游民、唯美的疾病患者
你写下自度曲
风吹草动,姜白石沦为食客
你的秃头,集体主义的空白
喝二两酒脸红,喝三两酒失踪
你这发福的身体
里面全是婚姻的过眼云烟
拿不起呀,也放不下
多少光阴是假的
多少头发可以扎两条南宋的长辫
梦想的灯泡在头顶
时代的下半身一览无余
脚手架、挖土机、运渣车
一环扣一环,吃、喝、玩、乐
精致的马桶应运而生
你似蹲似座,身体向内弯曲
尖锐的耳垂趋于宽大
哦,无产阶级的中年
书可读,人可数
翻过一页,碰到树,老树发新芽
墙上的木刻:鱼
在白天,它是暧昧的。鱼刺卡住木头的喉咙
木头一直在用力
咽下桐油、钉子以及一小块墙壁
鱼倒挂。与客厅的一面墙相比,它是忧郁的
挤干了水份的鱼鳞趋向木纹
它的不规则正如空气的不规则
到了鱼尾,缺氧的船队一字排开
蚊子紧随其后,这袖珍的吸血鬼
在盘旋,在立秋之日扑向墙上的木刻
可惜,用力过猛
蚊子头破血流,它的江山已经皮之不存
鱼的江山呢?木头的江山呢?
它们结合得如此深刻,我一眼看出了破绽
没有江,鱼头就只有向下低垂
没有山,木头就只有方方正正
现在看来,蚊子、鱼、木头聚到一起
不是出于偶然,而是那四颗钉子
这一天,堵住了东西南北,堵住了它们的来和去
和解
和一支铅笔和解,我写的字可以擦去大半
和这恶劣的一天和解,我裤脚的泥浆可当布料
和一个人和解,我说过的话可以石沉大海
和自己和解
我不再是你,也非遇事都是过来人
尽管你愤怒过、爱过、水泥板上睡过
如今你要和往事和解
就得解开全身的扣子
赤身裸体,于月照之夜
一再擦拭体内的暗斑
蝴蝶之歌
蝴蝶曾经在我的诗中出现过,那是1989年
我即将离开大学,失败的四年
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蝴蝶。首先是
这两个汉字天生丽质,其次才是那飞翔
路途变得变幻无常,这虚空的美丽
吸纳着农药、花粉和被我们污染的空气
但我们良莠不分,把蝴蝶比喻为
低空飞行的天使,实际上,谁也没有看见过
天使。被虚构的蝴蝶,在今天看来
就是被夸大的青春,它薄薄的羽翼尽善尽美
它扇动时,黄昏趋向透明。
它静止时,花朵迅速凋零。
一物对另一物的影响总是悄无声息
一只蝴蝶的加入,肯定说明更多的东西在消失
我多想成为那消失的一样东西
隔着城市和黑暗,在蝶翅的一张一合中
用火柴擦亮夜晚,用泪水哭响春天
而换一个时间,也许就在1953年夏天
靠近亚利桑那州的一座农场里,蝴蝶一生的
多次蜕变被纳博科夫重新命名
它安慰着《说吧,记忆》在英语和俄语之间
的盲点(1)。不同的书写在同一只蝴蝶身上展开
这正是纳博科夫为我们描述的蝴蝶之谜
一条林间小路,一群褐色蝴蝶
摹拟着树叶,她们是为了逃避捕获
还是在呈现一种难以释怀的迷醉?
(1)纳博科夫在自传《说吧,记忆》的不同语种的写作中,意识到一种语言的盲点很可能成为另一种语言美丽的焦点。
小镇春秋
小镇的灯熄了,夜很浅,漆黑的街道
右拐三百米,早年的小学还在
还有守门人。换了人间
这些年我在初恋之外,在外省
巴河减一点我的肚皮,山岗减一点我的身高
这不老不少的身子骨
腾出几把椅子,到了现在这般模样
能屈能伸,能在酒中打坐
小镇过春秋,我是寒假上山打柴的好学生
爱我者三教九流,往西,水陆空直上蜀道
我爱的人发育不全,不送别
她迟早是镇上引人注目的女青年
像番茄一样,甜透了一日再一日的午后阳光
我去意已定,小镇殿后
旧时的军用机场,放弃飞,放弃天空
数亩良田把它压在身下
即使想飞,我也必须先到武汉
也必须有一小片制空权
这些年,身体里的坡坡坎坎,节节陡峭
到了额头,小镇就一滴汗那么小
几乎不在,在路上,在湖北偏僻的角落
我沿着河堤慢行,今夜,我摸黑回家
小火车
听命于煤,听命于野草,听命于自身的缓慢
小火车上了山,正是落日时
没有人烟,没有时刻表要求它
从此地到彼地,春天的煤应及时送到冬天
风追它,风渗进煤层
石头追它,抄小路,一分为二,到天边
小火车局限在枕木上
它的局限是自己的,也是旁边万家河坝的
这时出没者,头顶探照灯
脚下的三米,是可以预期的深一脚浅一脚
再远一点,小火车搭上浮云
我们几个闲客,四处打听修鞋的师傅
小黄的高跟掉了。小火车跑出了铁轨
煤泻一地,乌黑的,油绿的,惨白的
山间之风貌,顿时滔滔,人、物俱有形状
唯小火车荒凉
黑洞
星辰不再闪耀。黑洞
撒开一张捕获的网,而它自身
如此细小。紧缩的入口,通向
天上偏远而秘密的省份
没有边界。黑洞就是时间的
另一面,像弹簧,可长可短
它果真有一个巨大的胃
消化星辰和陨石。而树木
逃逸。四季的气象四散
只有枝桠,长出夏天的侧影
那些无意泄露的星光,搁置在
青苔上。哦,漫长的后半夜
我身体里的黑洞回应着太空
被吞食的旧物一再演变。丝巾
成了纸片,钢笔如羽毛
飞越海市蜃楼。惊人的对称
诞生在偶遇。我看见还乡的人
没有故乡,过去的星辰,它曾经
试图述说一切,结果沦为
天空的盲点。在黑洞里蒸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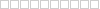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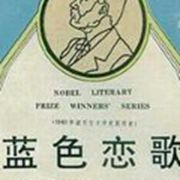 蓝色恋歌 评论 何房子自选诗 | 情种、游: 黑洞就是时间的 另一面
蓝色恋歌 评论 何房子自选诗 | 情种、游: 黑洞就是时间的 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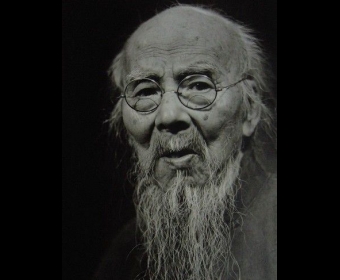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