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你一直跟在我身后
踩着我的影子走自己的人生路
如今你已五十了
路虽走得长可仍就矮得像只乌龟
有时你鼓足勇气走在我的前面
我就不知不觉走上了斜道
你教坏我两个儿子
气死我一个丈母娘
你仍是我最好的兄弟
多年来你一直睡在我客厅
帮我挨刀挡枪过着侠客的日子
如今你知天命了还把自己当老婆
有时你依然是个哲学家
你冷嘲李白热讽徐志摩
说诗歌不能当饭吃
你是想让老子走老路去赚钱
你好重新过上吃喝嫖赌的日子
只可惜你的人头长不到我的项上
多年来你跟在我句子后面像个标点符号
帮我传递着意犹未尽的表述
其实你早已大半截身子入土了还食不饱肚
一顿当作三顿吃 三天当作一天过
有时你把老子当天才在看待
有时却把老子当弱智在打发
你说老子两个是尝尽人间百味的人
要吃就吃苦 要么就吃人
说得自己像坨棉花刀枪不入
矮子 想起你笑过之后我就想哭
我枉自比你高这么多
不能为你撑起一片生活的蓝天白云
今夜我独自走在你生日的雨中
身体仿佛是一只巨大的伤口
漫天的雨水象一盆盆盐水直往口子里泼去
疼得我骨头也一阵阵痉挛
我不得不向过去弯下腰去
矮得比你还矮
九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每每想起这样苍凉的句子,我就难免要感怀80年代大学生这一代朋友的奇特际遇。二十多年来,无数人载沉载浮,大起大落,生死相许,不少的弟兄甚至墓木已拱。现在我们也开始步入中年,当日英雄渐白头,转顾曾经的风云往事,常常想不起究竟是怎样在这个诡异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中年失路的王七婆,一定是在某个酒阑之夜猛然大澈大悟,被诗歌那一盏亘古相传的青灯又再次照亮了。名句曰——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他混入江湖的起点似乎源于诗,现在他急流勇退的靠岸点,依旧还是诗。他的一位江湖大哥,为了鼓励他金盆洗手回归诗歌,不惜免去了他的百万债务。但是尽管如此,诗歌在这个国度除非被御用,否则依旧难以养命。道上行话说:换帖子容易拔香头难,讲的还不只是一个放不下的问题,更多的回头者,难在找不到可依之岸。
在他的诗集出版之夜,他在电梯里邂逅了他今天的少妻。这个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子,竟然神奇般地爱上了这个一身匪气却已两袖空空的男人。良人者,妻子所以托终身也。当下立地转世的王七婆,终于决心要做一个良人了,可良人得要有良人的活路才行啊。江湖人的本事,讲的就是个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天知道这厮啥时学过美术,突发奇想开始油画了。虽然最初的作品,多由各码头的老大买走,但老哥们私下依旧觉得他不过是在闹着玩,认为那些买家也多是在还他当年的袍泽之情。
哪知道几年下来,他越陷越深,作品参展,还获金奖——这让我开始吃了一吓。本质上,我是一个美术的外行;乡村世界的品评——只看你画得像不像。如果他上手就是抽象派,玩概念随便涂抹颜料,那我还是难以确信。孰料把他的作品找来一看,还真不是那种蒙人的线条结构色块之堆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现在要他去乡码头支一个摊子,专为农家画先祖亡灵,他那准确且神似的手段,都能从乡亲们兜里掏出钱来——这才是真本事。
我最近在给他的一个短简中戏说——这个社会想要把你娃逼死,看来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一拨兄弟也许真没有改天换地的本事,但飘风泼雨地杀将过来,确实都混成了一粒煮不烂捶不扁的铜豌豆。任是如此,从良的男人和女人一样,也都各有各自的尴尬和困窘。
正如他的诗中所说——一个人走在四个矮子中间混迹道上,不敢说性格是刀削出来的,不敢保证眼泪掉下来不砸伤人,更不敢酒后逢人就摆大型龙门阵。 一个人用药下酒毒死夜晚的孤独,不敢在憧憬的时候露出回忆的神色,不敢说曾经怎样也不敢说将来咋,更不敢说人生醒和醉都是场误会。 一个人娶三妻生两子,不敢刨初恋的根,不敢让老婆听见前妻的电话,更不敢修座四合院把三妻四妾用一道门围进来。 一个人黄泉路边开客栈,鬼门关口摆夜市,不上天堂不入地狱,更不从中生离死别。
许多年前,他有名句曰——带刀的男人,不带表情,带着偏执与狂傲,向未来砍开通行的路。如今,几十年砍砍杀杀下来,他感叹的依旧是——路边有三朵野花,一朵是我,一朵是妻,一朵是女儿;我们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他一边行走江湖,一边在心底构思诗画,他终其一生似乎都想和谐地处置好自己。然而生活的荒谬,往往如其所说——当政权和我发生摩擦时,我选择了远离专政的心脏最大限度地绕道而行;在一个绝对生存的高度怀揣一颗圣洁的心,把自己绕进了雪域的牢房。
最后,我想说——琪爷,我们也该老了;白发江湖,我能为兄弟你写的,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往事,该你自己慢慢反刍,和血吐出来咀嚼吧。如果我们这一代都自个悄然刨灰,无声地埋葬自己,我们的儿孙何以知道,我们曾经历怎样一个三刀六洞的时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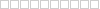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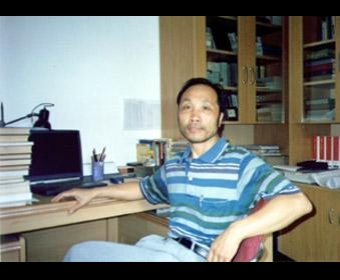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