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90年代下旬,中国进入房地产的疯狂年代。一路颠沛追赶着商潮的王七婆,这次似乎抢占了先机。他和几个老把子合伙,开办公司,收购土地,预售楼花,几乎兵不血刃就再次白手起家了。
几千万到手,一时财大气粗,竟日挥金如土。这厮仿佛天生跟钱结仇,不糟践一空便觉得人生无趣。虽然弟兄们跟着好吃好喝,难免也有江湖老客开始觊觎他的出手豪迈。赌局越来越大,陷阱自然也越来越深了。王七婆的赌兴和赌品,都是千客的最佳食材。昏天黑地的雀战,闭户关机地厮杀,三天输走两百万,等回到人间时,传来的却是母亲服药自杀的噩耗。
他的母亲早在他被大学开除之日,就闻讯摔倒,从此闹下浑身颤抖的余疾。晚年瘫痪,长期卧病于床,最终选择了尊严的死。十几年过去后,他跟我讲起这一段隐衷时,仍旧止不住哽咽涕泣。若干年之后,他在诗中怀念母亲——妈妈 自从你离开人世后 我便是一个被两串泪珠挂在凄凉上的孤儿 天好高地好厚 我怕 我怕掉下来砸得粉碎 我最怕将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到下一个世界去见你……
母亲的离去,终于催他迷途知返。他带着数目不菲的余钱,北上京都创办新国服服装公司。他像一个民族主义愤青一样,要振兴唐装中山装事业,打出了响亮的“穿国服,扬国威”的广告。最后,国威尚未扬起,他的国服却终于破产倒闭。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空空两袖地再次回到重庆觅食。
他的好运气似乎在前半生已被他挥霍一空,新世纪以来,他几乎是喂猪则牛涨价,养牛则猪升值——反正总是喂不到那个点上。当日弟兄见他落魄,又投资给他在重庆办服装公司,三个月就血本无归。他是那种掷骰子押单就非要一直押到底的赌徒,自认为精通服装业门道,又移师上海开锣。结果三百万现大洋,连个水响都没有听见,就沉落在上海滩了。
一生不肯认输的他,只好再次铤而走险。东拼西凑了一点本钱,单枪匹马闯缅甸,他想在那些百家乐的场子里,重新找回幸运之星。结果欠了放水的高利贷,被护场子的黑帮要活埋。幸好当年阔绰时待弟兄们不薄,千里呼救之际,还有忠义的矮子提着几十万赶来赎命,这才把他从齐腰的黄土中挖了出来。
正如他的诗所云——多年来我在缅甸和澳门的漫漫长路上,固执地单跳着。在零到玖的简单加减中轻狂地吹吹顶顶,先后吹脱了家庭,吹毁了前程,顶起了厚重的债务……
死里逃生的王七婆,回想当日富贵真是恍若隔世了。就在他决心金盆洗手,重新埋头写诗,并把几岁的次子培养成围棋业余五段高手之时。他那在成都长大的长子,在初中不甘忍受高年级的欺负和勒索,跟他年轻时一样组织群殴,结果刀下一死两伤。还未成年就要面对审判;四年少管刑期的终审,剥夺了这个愤怒少年的单纯时光。兰因絮果,仿佛一切都是血统中的宿命。开始探监孩子的他,似乎这时才顿觉英雄老去,机会不再了。其诗《围棋》开篇就写到——我大儿执黑小儿执白/我左手下黑右手提白/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力图走上正道……
前几年,明显沧桑了的王七婆,赶去成都接他的儿子出狱。我和李亚伟等大群哥们,为他们父子劫后余生的重逢接风。他那还只有高中生年纪的儿子,已然沉默寡言如成人。他略显歉疚地为儿子夹菜,儿子陌生无言地不愿正视这种迟来的父爱。对此两代人都躲不过的囚徒命运,举座黯然。
八
王七婆和我一样,几乎同时在遍历甘苦之后,选择了回归青春钟爱的文学。这时的我们心已老去,文字才终于开始成熟。他难得寂寞地整理完他的诗集《大系语》,交给我责编付梓。他在卷首献词中赫然写道——只要我一开始写诗,这个世界就要死人。
他的诗确实是这个平庸世界少见的江湖浩歌,每一个字都生硬磕牙,翻阅之间隐然如听刀枪迸鸣,是一种荒野奔命和绝谷斗杀的惊骇之声。我的朋辈多是这个时代真正顶级的诗人,当他重返诗坛时,许多人为之一震——这确实是一头硬鸟,能让人尿筋都散了。他的诗有浓厚的江湖气,格局和气场都十分霸道。比如:
今夜 大河奔流 南海北国相安无事,故乡走向黎明 路边的客栈醉了过客与老板娘。此刻谁的娇躯胆敢靠上我的肩,我将是他一生永远的依靠。 今夜我一人 等于万人同聚,今夜 我沉默 等于万声齐唱。今夜 我一个真小人,像伪君子一样坐着。
即便是一个刀光血影中打拼生活的人,其内心也不免儿女情长;古人说——钟情者正在我辈。王琪博的情诗和情事,也多是江湖上的佳话。他能用近乎强盗的方式表达爱情,这样的独门暗器,确确乎胜似春药麻沸散之类古方。他在用诗写成的家书里这样表白——前生给你一张过时的地图,你就能在今世的生存夹缝找到纤细的我。时间纵然安排你晚到二十年,命运必然让我在该等你的时候多等你二十个春秋……来世提前给我一支笔一片云,我就能预先签下天堂里的责任承包田……
他给恋人的诗也是充满流氓气息——
我想通过努力 把你想进怀抱
你生于日期 成长为岁月
行走在桃花之上 睡在笔尖之端
我伤心时你徘徊在记忆的弯道上
你开心时我深陷在一首诗的结尾中
活着只为不与我正面相见
我想启动犯罪的方式扑到你身上
我想动用来世的资金控股你今生的婚姻
你若顺从就等于顺从了往后的日子
你若拒绝就从此拒绝了人间最美好的时刻
你真敢半推半就 那你不是骚货就是水货
就犹如一朵花长在枝头叫开放
掉在地上就得烂
不仅对女人深怀这种野蛮的柔情,本质上说,江湖中人托命于情义二字,也因此才有割头换颈的兄弟。矮子是他一生的至交,这个纯粹的道上人物,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曲真正令我读之酸哽的《矮子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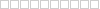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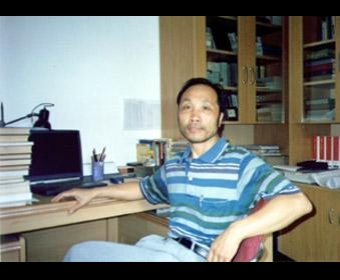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