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三十余年文化之变
余三定:对于新时期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从文化变迁的视角该怎么看?您不久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断裂”和“成功”,是很难放在一起的。
陈平原:首先需要说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动荡的状态。这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接下来,才有所谓“成功”或“失败”的文化断裂。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改变了这种独尊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些年则更多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可我认为,即便是“和谐社会”,也并不像桃花坞年画描述的那样“一团和气”,照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由“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构成的,有断裂也有连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把历史进程想象成“一路顺风”,那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的历史,实在太无趣。正是各种各样的断裂,造成某种意义上的间隔或跃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文化断裂。 其实,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好多类似的“断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5年的摒弃科举,还有废除帝制、全面抗战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某种断裂。新中国建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何纪念改革开放?不也是承认那是对“文革”历史的否定?今天这个“断裂”获得大家的认可,承认它是对10年“文革”的终结,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余三定:怎样理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陈平原:毫无疑问,30余年前开始的那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比如说,如果你关注文学艺术,你会记得,1985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时候,“文革”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开始独立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涌现出来的。经历过对西方文学、学术的热烈拥抱,到这个时候,逐渐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1985年对于文学艺术、人文学术而言,绝对是个重要年头。至于经济史或社会学家,你肯定关注1992年。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你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起草文件时,建议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因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了。这个建议被高层接纳,江泽民总书记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字的差异,此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选择不同的“关键年份”,意味着你谈论“三十年”时的观察点,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立场与思路。所以,所谓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假定的论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缝隙,进入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与阐释方式,这才可能呈现千差万别、五彩斑斓的“三十年”。
充分正视我国目前办大学的“误区”
余三定:我在前面提到,您近十多年来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在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独特的、深刻的见解和观点。其中您关于办大学的“误区”的分析就非常尖锐而深刻,希望您能具体谈谈。
陈平原:我以为,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
余三定:您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您有何感想和看法?
陈平原: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倡导并积极探索文学讨论课
余三定:5年多前,我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读到过您的散文《“专任教授”的骄傲》,该文写道:“2006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说您十分乐意当一位“专任教授”,您确实也是北大特别受欢迎的“专任教授”。我记得1992-1993学年度我在北大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的那一年,每周都去听您的课,从未间断,至今仍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您特别提倡文学教学的讨论课,希望您具体谈谈讨论课。
陈平原:讨论课就是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余三定:请您谈谈北京大学的讨论课。
陈平原: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但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余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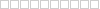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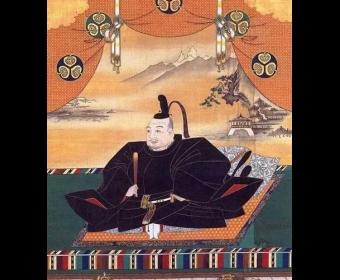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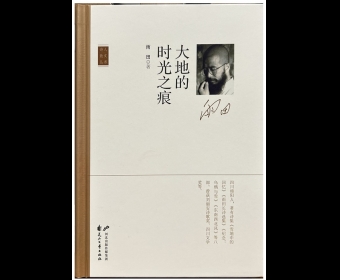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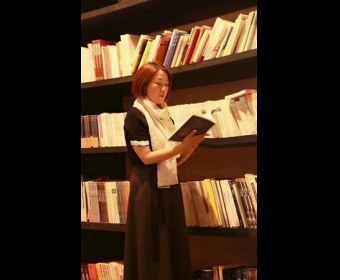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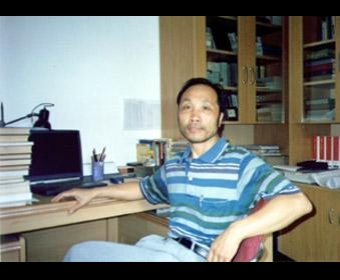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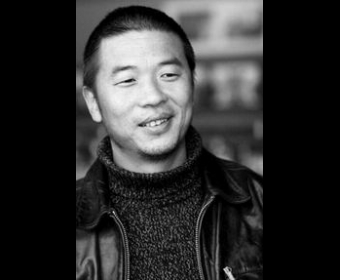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